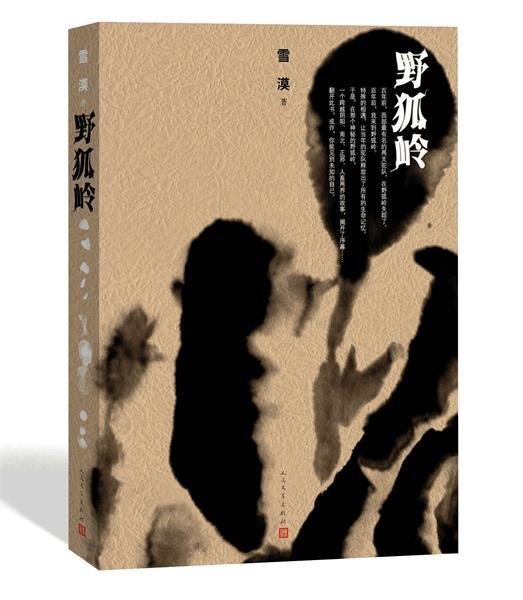
直面历史苦难与人性困境的灵魂叙事
——评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虽然肯定称不上著作等身,但刚刚年届五十的作家雪漠,其小说写作数量在同龄人中却无疑是可以名列前茅的。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长篇小说这一种文体,他截至目前就已经有七部之多。其中,《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一般被称为“大漠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则被称作“灵魂三部曲”。这部新近创作完成的《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乃是第七部。遗憾处在于,尽管雪漠在自己的小说写作历程中,不断地在思想艺术上做出过多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我对他小说写作的深刻印象却依然停留在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大漠祭》上。虽然已经时过多年,但当时那样一种“惊艳”的感觉却仍然仿若昨日般记忆犹新。之所以会“惊艳”,就是因为在那部相当典型的西部小说中,雪漠毫无伪饰地以一种质朴无华的艺术形式把西部乡村世界原生态式的生存苦难足称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大漠祭》之后,《猎原》与《白虎关》的具体书写对象,依然是那片广袤无垠的西部大漠。虽然文本中也一样有着对于生存苦难的真切逼视,但因为已经有《大漠祭》在先,雪漠的此类同质化书写便无论如何都难称超越了。然后,就是所谓的“灵魂三部曲”了。就其基本的思想艺术特质而言,更加看重于艺术想象力发挥的“灵魂三部曲”,较之于以写实为显著特色的“大漠三部曲”,确实极其充分地凸显出了作家一种自觉的超越性努力。但或许是因为这几部小说由于有所谓宗教情怀的介入而显得过于凌空蹈虚的缘故,以至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会对雪漠这个系列的作品形成一种“走火入魔”的感觉。如此看来,尽管雪漠在《大漠祭》之后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一种思想艺术上的自我超越,但实际的成效恐怕却是要大打折扣的。一直到这次认真地读过《野狐岭》之后,我才不能不承认,依凭着这样一部沉甸甸的厚重文本,雪漠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思想艺术自我超越的宿愿。尽管未必认同她的全部判断,但从总体感觉而言,我以为责编陈彦瑾的结论还是比较靠谱的:“我相信,对于雪漠来说,《野狐岭》的写作是一个挑战,也将会是一个证明。由于它,雪漠实现了许多人的期待——将‘灵魂三部曲’的灵魂叙写与‘大漠三部曲’的西部写生融合在一起,创造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和”的文本;由于它,许多认为雪漠不会讲故事的人也将对他刮目相看,并由此承认:雪漠不但能把一个故事讲得勾魂摄魄,还能以故事挑战读者的智力、理解力和想象力。因此,我断定,《野狐岭》将会证明:雪漠不但能写活西部、写活灵魂,雪漠也能创造一种匠心独运的形式,写出好看的故事、好看的小说。”
陈彦瑾的上述看法,无论是认定雪漠的《野狐岭》创造了一种匠心独运的艺术形式,抑或还是认定《野狐岭》从根本上实现了一种思想艺术上的自我超越,皆属于切中肯綮之言,我自然完全认同。我所不能认同者,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所谓的“西部写生”。小说中存在着明显的西部因素,这一点诚然毫无疑问,但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部西部小说呢?尽管我知道,其他一些人也会如同陈彦瑾一样坚持认为《野狐岭》是一部成功的西部小说,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如果仅仅把《野狐岭》视为西部小说,实际上就看轻了这部小说的高端思想艺术价值。很大程度上,所谓的“西部写生”也只不过是小说的外壳而已。借助于西部大漠这一外壳,跃入存在的意义层面,在这一意义层面上传达表现作家对于生命一种真切的思考与体验,方才应该被看作是雪漠最为根本的思想艺术追求之所在。与其说《野狐岭》是一部西部小说,反倒不如说是一部对于人类的生命存在进行着深度艺术思考的小说更恰当一些。在一篇关于史铁生遗作的文章中,我曾经写到:“在具体分析史铁生的作品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有所讨论。这就是,文学的根本功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我特别注重于文学对于现实的呈现与批判功能。而且,据我所知,一直到现在,也仍然有许多人在坚持这样的一种基本理解。但是,面对着史铁生的文学创作,我才渐渐地醒悟到,其实,从本质上说,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关乎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应该是一种对于生命存在的真切体悟与艺术呈示。史铁生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一向具有着这种艺术品质。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点,在作家的这一组遗作,尤其是《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某种意义上,这部未完成的长篇作品应该被看作是史铁生面对生命时的一种玄思冥想。” 客观公允地说,文学也应该有对于社会现实的呈现与批判功能,尤其是当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存在形态还存在极严重问题的时候。但与此同时,一种具有突出超越性的对于生命存在的体悟与呈示,却同样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根本功能。对于雪漠的这部《野狐岭》,我们很显然更应该在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分析。其二,则是关于雪漠讲故事的判断,认为一向被认为不会讲故事的雪漠终于可以把故事讲得“勾魂摄魄”了。作为一种典型不过的叙事文体,小说要讲故事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已有丰富小说写作实践的雪漠来说,他讲故事的艺术能力绝不是到了《野狐岭》才表现得非常突出。但更重要的,恐怕却是由陈彦瑾的这一判断而引发出的小说观问题。就陈彦瑾之一力强调雪漠终于写出了“好看的故事,好看的小说”而言,能否写出“好看的故事”,显然是其小说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构成因素。但在我看来,判断小说优秀与否的标准,绝不仅仅只是能否讲述“好看的故事”的问题。能够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居然可以达到“勾魂摄魄”的程度,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一种艺术能力,但真正优秀的小说却绝不仅止于只是讲述“好看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说,能够把故事讲得“勾魂摄魄”只是优秀小说所应具备的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作家所欲传达出的思想内涵是否足够深厚,作家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究竟抵达了何种程度,恐怕才是衡量评价一部小说作品的重要标准之所在。而雪漠的这部《野狐岭》,则毫无疑问正是这样一部在“好看的故事”之外有着足称丰厚的思想精神内涵的长篇小说。
从题材上说,《野狐岭》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历史长篇小说,作家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百年前发生在大西北凉州地面上一场反抗满清政府的历史事件上。但在具体展开对文本的分析之前,我们却也不能不指出小说存在着的艺术败笔。具体来说,这败笔也就是指关于那场发生在岭南的土客械斗的艺术设置。小说的主体故事本来发生在大西北凉州的沙漠之中,但雪漠的笔触却不能不从遥远的岭南写起。之所以会如此,与当下时代文坛所普遍流行的项目签约制度密切相关。我们注意到,在作为“代后记”的《杂说<野狐岭>》一文中,雪漠开宗明义地写到:“《野狐岭》虽然是东莞文学院签约项目,但其中的主要内容,如凉州英豪齐飞卿的故事等,我酝酿了很多年。”既然是东莞文学院的签约项目,那就无论如何都得与东莞发生一点关系。关键在于,一个主体部分发生在大西北的小说故事,怎么样才能够与遥远的岭南东莞发生关系呢?为了达至这样的一种艺术目标,雪漠不惜煞费苦心地设定了那场土客械斗。由于土客械斗的起因,乃是小说女主人公木鱼妹一家与岭南富户驴二爷一家的矛盾冲突,所以,借助于那场土客械斗的设定,雪漠也就连带着把木鱼妹与驴二爷这两位主要人物引入到了小说文本之中。那场土客械斗的直接起因,乃是因为木鱼妹家的祖屋某一天被一场人为的纵火给烧掉了。由于此前驴二爷曾经反复再三地试图把木鱼妹家的祖屋买到手,也由于驴二爷曾经占有过在他们家做厨娘的木鱼妹母亲,所以,木鱼妹自然也就把这笔账记到了驴二爷的身上。因为父亲母亲都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变成了“焦棍”,为家族复仇的使命自然落到了木鱼妹的肩头。怎奈由于缺乏必要的证据,木鱼妹坚持不懈的告状一直无果:“虽然我明白凭我个人的力量,要跟驴二爷较量,等于凡人跟老天较量,但我还是义无反顾。我四处奔波,见衙门就进,见官员就拜,我感动了很多人。他们都愿意帮我,但他们的帮也改变不了事实。没有足够的人证和物证来证明驴二爷是杀人凶手。”惟其求告无门,万般沮丧的木鱼妹才常常会忍不住大哭出声:“我觉得那是我的心在哭。我想到阿爸很苦的一生,就忍不住会痛哭。我总是会想到一个文人在命运的无奈中遭受的污辱。我的哭声感动了好多人。有人甚至认为,后来新一轮的土客械斗,就跟我的哭有关。”但究其实质,木鱼妹的家仇,也只不过是那场土客械斗的导火索而已:“本来,家乡的土人就一直对驴二爷不欢喜。因为他一个外来人竟然拥有了那么大的家业,成了人上人,好些当地人心理很不平衡。他们一方面也会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巴结驴二爷,另一方面心里的不平衡也慢慢变成了仇恨。他们更眼红驴二爷的财富,一直想找个理由和契机。我家的故事,就成了一个理由。”就这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来只是木鱼妹个人的家仇,但由于家乡土人一种普遍的不平衡仇富心理作祟的缘故,终至最后燃起了土客械斗的熊熊大火。尽管因为有官家的强势介入,那场血腥的土客械斗最后被弹压下去,但驴二爷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还是离开岭南返归凉州了:“那次血腥事件平息之后,驴二爷回老家了。他是随着驼队来的,又是随着驼队走的。他安排了一个账房先生管岭南的商务,他自己,却不敢待那里了。无论他后来如何施粥,土人还是忘不了他的那些枪手欠下的血债。好些人,都想要他的命。这样,碉楼虽然安全,但他要是待在里面不出,也就等于坐牢了。权衡再三,他还是回老家了。”驴二爷一走,木鱼妹的仇人也就消失了,她还怎么能够实现报仇的愿望呢?正是由于内心里有着刻骨仇恨的强力驱动,所以,木鱼妹才一不做二不休,义无反顾地追随着驴二爷的脚印也踏上了前往大西北凉州的迢遥路途。这样,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也就由岭南而牵移到了大西北的凉州沙漠地带。“野狐岭”也才因此而得以浮出水面。
非常明显,作为一部旨在透视表现百年前哥老会在凉州地面反抗满清政权那个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野狐岭》的叙写重心绝对应该落脚在拥有齐飞卿同时也拥有野狐岭的凉州地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雪漠关于岭南故事的叙写其实并无必要。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作家的岭南叙事读来总是难免会有一些牵强生硬的感觉产生。这一点,在陈彦瑾的感觉中其实也能够得到相应的证实:“相形之下,雪漠也想记录的另一民间文化载体——岭南木鱼歌则逊色很多。毕竟没有真正融入岭南,雪漠对岭南人的生存和岭南文化的描写,和《西夏的苍狼》类似,还只停留于表面,远不如他写故乡西部那般出神入化、鬼斧神工。” 这样的一种事实就再一次证明,作家只有在描写表现自己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时候,方才能够获致一种如同神灵附体般的艺术灵感。一旦远离了这种真切生命体验,他的笔触就可能变得特别迟钝。然而,正所谓瑕不掩瑜,尽管岭南土客械斗故事的插入的确显得有些牵强生硬,但这却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野狐岭》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功。
《野狐岭》的思想艺术成功,首先体现在对于一种叙述形式别出心裁的营造上。虽然小说所要表现的核心事件是齐飞卿的哥老会反清的故事,但雪漠所可以选择的叙事切入点,却是对于百年前两支驼队神秘失踪原因的深入探究:“这两支驼队,是当时西部最有名的驼队,一支是蒙驼,一支是汉驼,各有二百多峰驼……他们遭过天灾,遇过人祸,都挺过来了。他们有着当时最强壮的驼,他们带着一帮神枪手保镖,枪手拿着当时最好的武器。他们更有一种想改天换日的壮志——他们驮着金银茶叶,想去俄罗斯,换回军火,来推翻他们称为清家的那个朝廷。后来的凉州某志书中,对这事,有着相应的记载。但就是这样的两支驼队,竟然像烟雾那样消散了。很小的时候,我老听驼把式讲这故事,心中就有了一个谜团。这谜团,成为我后来去野狐岭的主要因缘。”如此久经历练的两支驼队为什么会神秘失踪呢?“很小的时候,我老听驼把式讲这故事,心中就有了一个谜团。这谜团,成为我后来去野狐岭的主要因缘。”为什么是野狐岭,因为野狐岭正是百年前那两支驼队的最终消失之地:“几个月后,他们进了野狐岭”“而后,他们就像化成了蒸汽。从此消失了。”关键问题在于,既然那两支驼队早在百年前就已经神秘失踪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他们的失踪之谜弄明白呢?这样,自然也就有了招魂术的“用武之地”。“进了预期的目的地后,我开始招魂,用一种秘密流传了千年的仪式。大约有十年间,在每个冬天的每个冬夜,我都要进行这种仪式。……我总能招来那些幽魂,进行供养或是超度,这是能断空行母传下来的一种方式。”“我点上了一支黄蜡烛,开始诵一种古老的咒语。我这次召请的,是跟那驼队有关的所有幽魂——当然,也不仅仅是幽魂,还包括能感知到这信息的其他生命。”“我”之所以能够招魂,原因在于,“世上有许多事,表面看来,已消失了,不过,有好多信息,其实是不灭的。它们可以转化,但不会消亡,佛教称之为‘因果不空’,科学认为是‘物质不灭’。于是,那个叫野狐岭的所在,就成了许多驼把式的灵魂家园。”惟其如此,凉州一带才会广泛流传这样的一个民谣:“野狐岭下木鱼谷,阴魂九沟八涝池,胡家磨坊下取钥匙。”很大程度上,这个广泛流传的民谣,正是雪漠写作这部《野狐岭》的基本出发点。“那所有的沙粒,都有着无数涛声的经历。在跟我相遇那一瞬间,它们忽然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记忆。在那个神秘的所在,我组织了二十七次采访会。对这个‘会’字,你可以理解为会议的‘会’,也可以理解为相会的‘会’。每一会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劲头大,就多聊一聊;有时兴味索然,就少聊一点。于是,我就以‘会’作为这本书的单元。”
实际上,也正是凭借着如此一种招魂行为的艺术设定,雪漠非常成功地为《野狐岭》设计了双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招魂者“我”(也即雪漠),是第一层的叙述者。而包括木鱼妹、马在波、齐飞卿、陆富基、巴特尔、沙眉虎、豁子、大嘴哥、大烟客、杀手(联系杀手所叙述的内容认真地追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个无名的杀手其实是木鱼妹。又或者,杀手与木鱼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结果),甚至连同那只公驼黄煞神在内,所有这些被招魂者用法术召唤来的百年前跟那驼队有关的所有幽魂,就构成了众多以“我”的口吻出现的第二个层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招魂者“我”正是通过这许多个作为幽魂的“我”从各不相同的叙事立场出发所作出的叙述,最大程度地逼近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作为第一层叙述者的招魂者“我”。为了在野狐岭通过招魂的手段有效地还原百年前的历史现场,招魂者“我”可谓历尽了千难万险。在生存条件特别严酷的野狐岭,招魂者差不多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某种意义上,招魂者所遭遇的艰难处境与百年前那两支驼队的生存苦难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相互映照的对应关系。雪漠对于招魂者处境艰难的艺术表现,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那两支驼队在百年前的神秘失踪。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那些幽魂的叙述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到招魂者的精神世界。“我被木鱼妹的故事吸引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除了木鱼妹外,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在波。在把式们的记忆中,他一直像临风的玉树”“我最希望自己的前世,是马在波”“只是,故事越往前走,我越发现,自己可能是故事里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讲的故事,我听了都像是自己的经历,总能在心中激起熟悉的涟渏。这发现,让我产生了一点沮丧。”究其根本,招魂者“我”之所以会对那些幽魂们产生渐次强烈的认同感,会以一种“前世今生”的方式认定“自己可能是故事里的任何一个人”,就意味着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无法抗拒来自于幽魂们的影响。
然后,就是那些一直在进行着交叉叙事的第二个层次的幽魂叙述者。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迥然不同于他者的精神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类个体从不同的精神立场与观察视角出发,所看到的自然是差异明显的景观。更大的事件且不说,即使是给骆驼做掌套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在陆富基看来,理应是蒙驼队的大把式巴特尔为这一事件负责:“为了保护驼掌,巴特尔弄了好些牛皮,给驼做了掌套。他的心当然是好的,可是,就是他的做法,让整个驼队瘫痪了。”因为,“那窝在掌套里的石子,几乎弄烂了所有的驼掌。”驼掌弄烂了,自然无法继续前行,只能被迫停留在野狐岭,而“噩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在马在波看来,这事情却无论如何都怪不到巴特尔头上:“那弄掌套的方法是我想出来的,不怪巴特尔”“我仅仅是想保护驼掌。我没想到,那些石子会贼溜溜地钻进牛皮套里,将那些掌们咬得血肉模糊”“这事儿,怪不得巴特尔。要说责任,还是我来承担”“我当然没想到,那驼掌的烂,仅仅是导火索和雷管。它引发的,是许多因素构成的炸药。”与掌套事件相比较,更为典型的,恐怕却是关于木鱼妹那样一种可谓是差异极大的理解与判断:“在对木鱼妹的解读中,就有着境界的高下:在木鱼妹自己的叙述中,她是以复仇者的形象出现的;大嘴哥眼中的木鱼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而马在波眼中,木鱼妹却成了空行母。”不同叙述者眼中木鱼妹形象的差异之大,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叙述者的话语权问题。关于小说中叙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曾经有论者写到:“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之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 在这里,论者颇具说服力地论述了叙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问题。雪漠之所以要在《野狐岭》中设置如此之多的叙述者,正与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关系密切。那么,对于雪漠在叙述者设定方面的积极努力,我们究竟应该予以怎样的衡估呢?必须注意到,如同《野狐岭》这样在一部作品中设置众多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形,在现代以来的小说作品中其实屡见不鲜。究其实质,可以说是小说艺术形式现代性的一种具体体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把众多的人物设定为叙述者,就意味着赋予了他们足够充分的话语权,是对于他们各自主体性的尊重与张扬。在充分尊重人物主体性的同时,因为把阐释判断事物的权利最终交付给了广大的读者,所以,如此一种分层多位叙述者的特别设定,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于读者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正因为这种艺术设定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于人物与读者的双重尊重,所以自然也就成为了小说所具现代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对于雪漠《野狐岭》中分层多位叙述者的艺术设置方式,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但千万请注意,正是通过这些看起来歧义丛生的叙述,雪漠相当有效地复现着当时的历史现场。一方面,“木鱼妹越来越鲜活了。因为那些骆驼客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我也从木鱼妹的记忆中看到了把式们。他们互相的记忆,构成了一座宝库,为我提供着那个时代的讯息。于是,那些汉子就在我心中鲜活了。”
分层多位叙述者的特别设定之外,与小说对于生命存在主题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的,还有雪漠在后设叙事方面所作出的艺术努力。所谓后设叙事,就是指在事件已经完成之后的一种有点类似于“事后诸葛亮”式的叙事方式。所谓“事后诸葛亮”,其本意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的色彩,但我们在这里却纯粹是一种毫无褒贬的中性意义上的使用。因为生命是一种不可逆的发展演进过程,一般情况下,人只能够顺着时间之河走向生命的终点。依循一种正常的生活与生命逻辑,任谁都不可能对自己的人生做一种终结之后的再度省思。唯其因为不可逆的生命过程中充满着很多难以弥补的遗憾,所以人们也才会用“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把这种遗憾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但雪漠的值得肯定处,却在于,通过招魂术的巧妙征用,使得那些已经死去多年的幽魂们得以重新复现汇聚于当下时代的野狐岭,不无争先恐后意味地讲述着百年前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两支驼队神秘失踪的故事。这样一来,招魂者之外的其他那些第一人称叙述者,就既“入乎其内”,能够在历史现场以一种同步的方式感性地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又“出乎其外”,能够在时过境迁已然时隔百年之后的现在,以一种极度理性的方式回过头来重新打量审视当年发生的那些个历史故事。比如,汉驼的驼王黄煞神,对于同一件事情,就有着前后对比极其鲜明的不同叙述。在汉驼驼王黄煞神与蒙驼驼王褐狮子围绕母驼俏寡妇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当时的黄煞神:“我当然要发怒了。要是你的女人叫另一个男人强暴,你会咋样?要是她带了一种半推半就的神态自家脱了裤子,你心里会咋样?你还说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母驼的扎尾巴,等于女人的脱裤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咋能不疯?”“我承认,我气坏了。记得当时,只觉得一股血冲上了大脑,脸一下子热了。”但到了时过境迁之后的当下时代,黄煞神的幽魂却冷静理性了许多:“当然,我的这种评价,是事隔多年后的今天,才做出的。而在当时,我是不承认它是驼王的。现在,等那诸多的情绪像云彩消散于天空之后,我的心才清明了,才能冷静地回忆当初。”“你要知道,好多事情,只要换个角度,就想通了。但有时候,那听起来简单的换角度,却不容易做到。现在,经了些事。当然想通了。但那时,我真的有些糊涂。”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雪漠对于后设叙事方式的特别设定,就使得那些曾经处于当局者位置的幽魂叙述者获得了一种类似于旁观者的澄明与通透。比如,在木鱼妹的叙述中,我们就能够读到这样的一些文字:“至今,我还没有发现关于王胖子如何为富不仁的证据,都说他为富不仁,但究竟如何个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多年之后,等我冷静下来后,才弄明白一个道理,在凉州人的心中,他的胖,本身就是烧他房子的理由。此外,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多年后的那场革命,你的富有,本身就是被专政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笑话,还在别处发生着。那时节,到处都有这样的暴动,他们面对强大的清家时,像小孩子面对一个壮汉。虽然壮汉只一拳就能击倒小孩子,但小孩子一次次爬起,一次次缠斗,扔鼻涕,啐唾沫,用各种方式攻击那壮汉,死了一个,又扑上无数个。开始,那壮汉浑不在意,但渐渐地,他开始疲惫了,渐渐像堕入了梦魇,他的步履开始蹒跚,终于在一次叫武昌起义的行动中被击中,倒地了。”《野狐岭》的主体故事是关于百年前两支驼队神秘失踪事件的叙述,无论是前一段叙事话语中的“就像多年后的那场革命,你的富有,本身就是被专政的理由”,还是后一段叙事话语中关于武昌起义的形象描述,从根本上说,都是拜雪漠恰如其分地采用了后设叙事方式的结果。究其实质,雪漠的《野狐岭》之所以能够以一种格外犀利的笔触揭穿社会历史与生命存在的真相,正与这种后设叙事方式的设定关系密切。
实际上,雪漠《野狐岭》艺术形式上的努力,还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对于分层多位叙述者以及后设叙事方式的特别设定上。诚如雪漠自己在《杂说<野狐岭>》(代后记)中所言:“《野狐岭》是一群糊涂鬼——相对于觉者而言——的呓语。当然,《野狐岭》写的,绝不仅仅是上面说的那些。其中关于木鱼歌、凉州贤孝,关于驼队、驼场、驼道、驼把式等许许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的一些东西,小说中的描写又有着风俗画或写生的意义。这一点,在本书中显得尤为明显,也跟我以前的小说‘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定格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一脉相承”,对于驼队、牧场、驼道、驼把式等的风俗画描写且不说,单只是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对于凉州贤孝与木鱼歌的堪称精妙的穿插与征用,就是非常有效的叙事手段。尤其是在叙述齐飞卿起义时,对于凉州贤孝《鞭杆记》的适度穿插,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极难忘的印象。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部分的叙述者,乃是天赋唱歌异秉的木鱼妹。历史上的齐飞卿起义,本就极具壮烈苍凉的意味,如此一种故事,被历经苦难折磨煎熬的木鱼妹以饱满的感情说唱而出,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真正是可想而知。关于这一点,只要认真地读一读第十二会“打巡警”与第十三会“纷乱的鞭杆”,我们即可以有真切的体会。但不管怎么说,雪漠对于所有艺术手段的设定与征用,其根本意图却都是,一方面要尽可能真实地逼近还原历史现场,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充分传达自己对于生命存在的理解与体悟,最终完成一种能够直面历史苦难与人性困境的灵魂叙事。
所谓历史苦难,落实在《野狐岭》中,就是指那场曾经名震一时的齐飞卿起义。而齐飞卿起义,从根本上说,乃是哥老会与清廷激烈对抗碰撞的一种具体体现。那次起义,缘起于齐飞卿他们的鸡毛传帖:“后来名扬凉州的那次暴动,就发生在那年的正月。那时,仅仅一夜间,一个歌谣就传遍了凉州:‘正月二十五,火烧凉州府,马踏上古城,捎带张义堡。’”“这次的鸡毛传帖,阵势很大,整个凉州百姓,差不多都收到了鸡毛传帖。”凉州百姓,之所以能够积极响应鸡毛传帖,参与到齐飞卿与哥老会主导的这场起义之中,一方面,固然与他们在清廷统治下艰难的生存困境有关。凉州贤孝有句云:“百姓们那时节实在也活不成,单等着提上脑袋大闹凉州城”,另一方面,却也与他们的一种宣泄与从众心理密切相关:“我发现,不容易起群的凉州人其实也爱起群——凉州人管抱成团叫起群。为什么?不容易起群的原因是没个起头的。大家管起头人叫高个子。只要有个起头的高个子,大家倒愿意把心中的激愤什么的,宣泄一气呢。”造反起义的结果可想而知,虽然赶跑了知县梅浆子,虽然起义的场面也的确称得上是轰轰烈烈,但在清廷派刘胡子的马队出兵镇压之后,本就是一团散沙的凉州人迅即就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了。起义以失败的悲剧结局告终,起义的发起者齐飞卿与陆富基只好无奈趁乱出逃。这样,也才有了后来那两支驼队的俄罗斯之行:“他们更有一种想改天换日的壮志——他们驮着金银茶叶,想去俄罗斯,换回军火,来推翻他们称为清家的那个朝廷。”而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身为哥老会重要成员的齐飞卿与陆富基,何以会出现在驼队之中。却原来,两支后来神秘失踪的驼队的根本使命,正是要颠覆强大的清廷。在这个意义上,两支驼队的因故未竟的俄罗斯之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齐飞卿凉州起义的一种后续行动。有了两支驼队的神秘失踪,方才有了百年后招魂者“我”的为了探明事件真相的野狐岭之行,进而有了这部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野狐岭》。
小说对于历史苦难的真切再现固然难能可贵,但相比较而言,更加值得注意的,却是在呈示历史苦难的过程中,对于哥老会反抗颠覆清廷行为的批判反思,是对于人性困境那样一种堪称洞隐烛微的观察表现。前者,在木鱼妹的叙述中表现得格外突出:“那时节,我信了飞卿他们的话,我以为,要是我们真的赶走了梅浆子,来个清官;或是灭了大清,百姓就会幸福。也许,正是因为我有了这一点善心,后来的坝里,才有了我的许多传说。他们为我修了庙,称我为‘水母三娘’。后来,我死后,因为人们的祭祀,我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关注着凉州。我睁着一双水母三娘的眼睛,看到了大清的灭亡,看到了民国的建立。后来,来了日本人,死了很多人。再后来,两兄弟又打架,死了很多人。再后来,一兄弟胜了。再后来,是一场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再后来,又是无休止的武斗,死了很多人。我一直在追问,我们当初的那种行为,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必须看到,类似的叙事话语,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多有体现。“不过,我这感悟,是后来的事。在鸡毛传帖的那夜,我还没到那种境界。要不是在过去的百年里,我不眠的灵魂经历了太多的事,我是不会有那种看破后的淡然的。人需要经历,没有经历的人,是不可能真正长大的。我的经历,让我有了另一双眼睛。对于我的说法,你可以当成一个百年孤魂的别一种哭吧。凉州人虽然尊我为水母三娘,其实你可以把我当成夜叉什么的。什么也成,一切,只是个名字罢了。”木鱼妹之外,比如陆富基:“那些天,飞卿很是着急。他急着要到达目的地,急着弄到军火,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对此,我很是不以为然的。从凉州贤孝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赶走乌龟,迎来王八。那些革命者,总是在革命成功后,变成另一个独裁者。有时候,那后来的暴君,甚至比前一个更坏呢。”再比如大嘴哥:“那些年,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平,我当然想改变这种状况。我当然希望推翻清家,但我没想到,推翻清家之后的日子更难过。民国也罢,再后来也罢,我并没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世界。没办法,我这个孤鬼,圆睁了眼,百十年了,也没看出一点亮光来。”正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木鱼妹、陆富基以及大嘴哥这些幽魂叙述者之所以能够对百年来的历史作出如此一种尖锐犀利的追问反思,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雪漠对于后设叙事形式的成功运用。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雪漠对于人性困境的洞察与表现。这一点,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齐飞卿起义中。虽然齐飞卿们以鸡毛传帖的方式充分发动民众参加凉州起义的出发点,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乃至颠覆清廷的统治,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预见到,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就极有可能会陷入某种严重失控的无序状态。还是在木鱼妹的叙述中:“我也知道,那抢人的、打人的、杀人的,只是乡民中的少数人,他们可能是混混、二流子或是穷恶霸,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是火种,他们一动手,其他人本有的那种恶就被点燃了。虽然人类个体不一定都有破坏欲,但人类群体肯定有一种破坏欲,它非常像雪崩,只要一过警戒线,只要有人点了导火索和雷管,就定然会产生惊天动地的爆炸。我发现,平时那些非常善良的人,那些非常老实的人,那些非常安分的人,都渐渐赤红了脸,像发情的公牛那样开始喘粗气,他们扑向了那些弱小的回民。他们定然想到以前死在回汉仇杀中的祖宗,他们将所有的回民都当成了敌人。他们想复仇。他们从最初的一般性抢劫变成仇杀。在集体的暴力磁场中,不爱杀生的凉州人,也变成了嗜杀的屠夫。”我们都知道,对于人类群体集体无意识中所沉潜着的人性之恶,法国学者勒庞曾经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揭示与剖析。在其中,勒庞的惊人发现是,个人在群体中很容易便会丧失理性,失去推理能力。到了某种特定的情境之中,个体的思想情感极易接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一句话,因人多势众产生的那种力量感,将会让个体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就此而言,雪漠《野狐岭》中关于凉州人在齐飞卿起义中的相关描写,就可以成为勒庞观点强有力的一种佐证。原本是善良的民众,结果却在某种集体力量的强力裹挟之下,最终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嗜杀的屠夫”。究其实质,其中那种无以自控的莫名力量,正是人类所难以超越的一种人性困境。
这种人性困境,也还同样凸显在雪漠关于那两支驼队发生内讧的艺术描写之中。内讧的起因,可以说与两支驼队中两位驼王之间的争风吃醋存在着直接关系。蒙驼的驼王褐狮子出乎意料地赢得了汉驼中一只年轻母驼俏寡妇的欢心,这就使得对俏寡妇情有独钟的汉驼驼王黄煞神气不打一处来,陷入了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作为报复,恼羞成怒的黄煞神,甚至不惜以犯忌讳的方式张口咬了褐狮子。关键在于,两位驼王之间的争斗,最终严重地影响到了两支驼队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是要为褐狮子复仇,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内心中贪欲之念的强力驱使,蒙驼队的大把式巴特尔终于决定把汉驼队的货抢到自己驼队:“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我们想开拔。为啥?我们不想叫汉驼拖死在野狐岭里。我们想前行。当然,我们也不仅仅想单纯地前行,我们还想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目的地,我们想单独做完蒙汉两家驼队应该做完的事。”对于自己如此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巴特尔的自我辩解是:“你想,我们问他们要那些他们已无力运送的货,是不是也有道理?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问题在于,巴特尔的背信弃义,固然令人不齿,但相比较而言,真正袒露出人性之不堪的,却是在巴特尔翻脸不认人之后,那些汉驼队中若干驼把式的恶劣表现。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蔡武和祁禄两位:“最先对陆大哥上刑的,就是蔡武和祁禄。蔡武话不多,老是笑眯眯的。祁禄则是个刺头儿,爱和人辩论。以前在驼队里,老陆一直在照顾着他们。但老陆是个直性子,有时说话是很冲人的,不知道是不是冲撞过他们?”在陆富基看来:“我可以理解蒙把式的那些勾当,毕竟,人家跟我们斗几十年了,从祖宗手里,就头打烂了拿草腰子箍。可汉把式,我们是兄弟,我们曾多少次地在包绥路上经历风雨,我们一同对付恶狼,对付土匪,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哪次不是同生共死。没想到,他们恶起来,竟然比恶人更恶。”无论是所谓“嫦娥奔月”,还是“倒点天灯”,皆属于蔡武与祁禄折磨自己同类的残忍手段。那么,既然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手足兄弟,蔡武和祁禄何至于如此呢?很大程度上,还是大嘴哥一语道破了天机:“蔡武和祁禄的家境不好,以前老陆常帮他们。也许,对老陆多次的帮,他们会感到很不舒服。有时候,在无奈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也许他们会想,凭什么是你帮我?欠别人的情多了,就会成为一种活着的压力。不然,我无法解释他们折腾老陆时的那种异样的热情。”却原来,对于别人的帮助,却也会在特定情形下给自己招来一种恩将仇报的不堪遭遇。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雪漠的这种艺术描写,的确淋漓尽致地发现了某种人性黑洞的存在。
也正是在目睹了这一幕幕充满着轮回报应色彩的人性卑劣惨剧之后,那些曾经的历史当事人、后来的幽魂“大彻大悟”了。在大烟客看来:“其实,我参加这次行动,只是职业道德使然。我虽然也是哥老会成员,虽然也认真地做很多事,但我只是做而已。活一辈子,我总得做些啥。但我明白,我的做,跟我的不做,差别不大。虽然你们常用一个新的名词,把那造反呀叛乱呀啥的,换成了‘革命’,但我知道,无论啥,都一样。都是想抢别人手中的那个印把子,都是想从别人那里抢财富,都是想当老爷。但你们当上老爷后,只会比以前的老爷更坏。”惟其如此,木鱼妹也才会生发出强烈的感叹:“你知道,这种追问,从那时起,我进行了几十年。我有那么长的寿命,便是在飞卿们死后,我还活了很多年。我见了太多的事。后来,那好不容易从野狐岭逃出的大嘴哥,也在几十年后被打成地主——谁叫他用当骆驼客的钱,买那些土地呢?遭了几十年罪,他才在某次挨斗的次日寿终正寝。当我听到他的故事时,我就产生了感叹,我觉得飞卿们,真的是白死了。”一切皆是过眼云烟,一切都最终会无着无落,借助于这些叙事话语,雪漠一方面格外强有力地实现着对于历史与“革命”“造反”的批判性审视,但在另一方面,读多了这些叙事话语,我们却也不难从中感觉到一种特别突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存在。就类似叙事话语在《野狐岭》中的大面积弥漫而言,似乎雪漠所持有的的确是一种充满着虚无色彩的历史观。
但是,且慢得出最终的结论,问题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虚无色彩的存在,在《野狐岭》中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在另一方面,通过木鱼妹与马在波故事的叙述,作家实际上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着对于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超越。木鱼妹与马在波的结缘,从根本上说,乃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怨恨复仇心理。由于一直怀疑自家屡次惨遭劫难的罪魁祸首乃是马在波的父亲驴二爷,为了报仇雪恨,木鱼妹不惜千里迢迢追随着驴二爷的步伐,从遥远的岭南来到了大西北的凉州。她的假扮乞丐婆,她的练习拳脚功夫,她的混入马府,其根本目的都是要锁定驴二爷实现自己的复仇愿望。怎奈天公不作美,她的以上诸般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之下,木鱼妹只好加盟到了哥老会之中。她的加盟哥老会,究其实质,目标也不过还是要复仇,要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复仇:“不过,后来我最想做的事,不是杀了马在波,而是让马在波加入哥老会,成为革命党,最后,被清家弄个满门抄斩,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复仇吗?那时节,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这。”也正是出于复仇的强烈愿望,木鱼妹方才追随着那两支驼队来到了野狐岭,千方百计地接近着马在波。但木鱼妹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越是接近马在波,就越是被马在波所深深吸引,甚至于从根本上丧失了复仇的意志。正因为强烈地感觉到了马在波那种人格魅力的巨大存在,木鱼妹内心中沉潜多时的仇恨意志才会渐次地被瓦解:“也许从我的讲述中,你们发现了我的变化:以前,我多希望能靠近驴二爷,给他致命的一击。为此,我想了许多办法也没能如愿。现在,我竟然怕他来了。为什么怕他来?怕他认出我。为什么怕他认出我?因为怕他打扰我现有的生活。”就这样,木鱼妹万般不情愿地发现:“我的心,竟然完全背叛了我”“以前,我想叫他造反,换来驴二爷一家被满门抄斩的结局。现在,叫他做同样的事的目的,却是想跟他在一起,同生,也能同死”“我不能忍受没有他的革命和造反。我只想跟他在一起。”就这样,木鱼妹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到最后竟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原本的复仇对象马在波。一个巴掌拍不响,关键在于,就在女性版的“哈姆雷特”木鱼妹爱上马在波的同时,马在波也爱上了木鱼妹:“我不管她过去是不是当过乞丐,我不管。我甚至不管她是不是刺客或是杀手。这是跟我不相干的一件事。我那时的心中,她就是一个可爱的女子。我倒是真的将她当成了空行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真是我命中的空行母。因为她激活了我作为男人的一种激情。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见过很多女子,有些也被称为美女,但她们是她们,我是我。她们打不破我的那种被罩入玻璃罩中的感觉。打碎那罩子的,让我感受到一种新鲜人气的,只有她。”到最后,也正是依凭着他们双方如此一种强烈执著的爱,曾经的仇恨被彻底地消弭不见了:“可他,又是我一生里最爱的人。因为他的出现,以前可爱的大嘴哥变丑陋了。因为他的出现,我硬冷的心变柔软了。因为他的出现,荒凉的西部不荒凉了。因为他的出现,生命有了另一种意义——超越于仇恨的另一种东西。同样,因为他的出现,我觉得野狐岭之行,多了另一种色彩。你别被我表面的语言迷惑,是的,我在用一种杀手的目光观察他,但以前我告诉你的那些,是我强迫自己想的内容。其实质,跟爱到极致的女子骂爱人‘挨千刀的’一样。”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雪漠关于木鱼妹与马在波之间传奇爱情故事的描写。有了这种描写的存在,作家对于生命存在的理解,显然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倘若说历史是虚无的,但情感的真切却无可置疑。雪漠在《野狐岭》中的相关艺术描写,甚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李泽厚关于“情本体” 的相关论述来。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应该从李泽厚“情本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雪漠关于木鱼妹与马在波的爱情描写。更进一步说,也正是依凭着这种强烈执著的感情,雪漠的《野狐岭》得以实现了对于历史苦难与人性困境的双重超越,实现了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生命救赎。
2014年11月20日上午9时4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5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