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任务。
论王德威现代华文文学史的困境
[美] 周春塘 文学报
今日推送文章为本周本报《新批评》专刊头条评论王德威教授的现代华文文学史研究,作者为美国华人文学教授,同时为便于从内部学界参照,也找来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多年前对王德威著作评论,以及王德威本人撰写的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梳理。三文对照,希望能够就此话题提供一个思考维度。——编者注)
■出现于二十世纪“新历史主义”的一些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存在了。王德威想替中国现代文学书写历史的宏愿,在尼采的新观念下,在记忆和遗忘的夹缝间,无疑会得到许多鼓励,也会面临不少的困境。
■王德威最爱引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但他大为推崇的作品,其简化人性的描写,都与巴赫金多元化的生命观背道而驰。我们的文学应如何跳出此一泥淖,争取新的活力,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王德威对此一问题的缄默,令人诧异。
■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家可以容忍曾阳晴、李昂文字上的缺陷,白薇、蒋光慈艺术上的失败,张大春写作上的懒惰,莫言、阎连科小说结构上的草率,不仅台湾文学的努力将是一场浪费,华文文学向世界进军的梦想,恐怕也将成为“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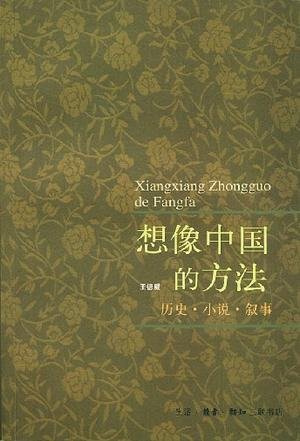
一
我无法低估历史的力量。尤其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拥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古老国度里,到了二十世纪,更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一如尼采所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断汇聚在一起,记忆敞开了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得不够宽”。(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一个正面接受这种历史挑战的学者便是王德威。他写下的专书和论文不下数十种,把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包括两岸四地,尤其是小说———这个最能反映历史经验的文体———交待得淋漓尽致。在他笔底,从晚清到民国,从1919到1949,从遗民到移民到逸民,从满清弃儿到亚细亚孤儿,从巫言到莫言,从伤痛到猥亵,从荒人到运尸人……说尽了现代海内外华人辛酸的故事和奇幻的漂流。生命对他而言,就是历史,而激情、乡愁,或者暴力、淫乱,不过是腥风血雨年代中不可或缺的插曲罢了。
在上面的引文中,尼采把“记忆”当做“历史”的同义词看待,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从他自称为《不合时宜的观察》的书中,尼采提出了生活就是历史,而历史服务于生活的概念; 在记忆和遗忘之间,造成了历史残缺不全的必然性,无形中也暗示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换句话说,出现于二十世纪“新历史主义”的一些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存在了。王德威想替中国现代文学书写历史的宏愿,在尼采的新观念下,在记忆和遗忘的夹缝间,无疑会得到许多鼓励,也会面临不少的困境。
在全球化呼声仍在持续中的今天,王德威期望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见证后现代以后小说千回百转的面貌”(王德威, 《当代小说家 II》 编辑前言),燃起了替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奠基立业的雄心,当然也将有他无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德曼在 《盲目与洞见》 一书中所说,书写文学史而提出现代性的话题,无异于把自己置身于“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现代性”这两个吊诡问题的夹缝间,最终难免要以意识形态当做武器,并给文学的理论做必要的交代。事实上,从王德威众多的文字著述中,我们知道他重视时代给予文学的冲击,也承担了时代“赋予”他崇高的使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众声喧哗的事实”。从此和谐与矛盾,本土与世界,传统与创新,这些后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复杂性,清楚浮上了台面。
以小说作为文学史的重心,确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向度。吾人无需钻入尘封的史籍,摩挲历史的丰碑,透过文本的阅读,便能见证时代的兴替,目睹暴力和创伤的消长。这些王德威称之为“嬉笑怒骂”、“感时忧国”、“风花雪月”或者“众声喧哗以后”书写而成的“虚构小说”,纵然偏而不全,仍是活生生的史页。这种文学语言,跟任何历史学家的语言相比,都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小说不再是“虚实不分”的语言游戏,或者《宋史·艺文志》所取笑的“虚诞怪妄”的“小说家流”。王德威致力于小说“新视角的开拓”,和“小说怎样来见证及介入历史”的研究,在此也得到了全盘合理的支持。
事实上,把小说扩充为“大说”的企图,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便已出现。王德威一再提到梁启超治群功用的“新小说”,和鲁迅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的言论,可知梗概。他后来居上,藉西方文学理论的他山之助,甩开了这种狭隘的文学实用论,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一个全新的维度。他在《小说中国》一书序言中说:
小说作者见贤思齐,要将小说化为大说的努力,从五四到当代也所在多有。但站在世纪末的边缘上,我们也许要说:大家听多了,来段小说吧。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世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2012)
他知道小说是虚构。但他承认“虚构总以生命及生活经验为前提”(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台北麦田出版,2011),也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它的功能足以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发生息息相关的联系。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内在的联系,随着外在因素的起伏,已不见了它们惯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福柯断裂、极限,和转变的历史系谱学(genealogy),遂成为他观察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的视野和方法。他庞大而良莠不齐的《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的诗文选集,从书名上看,便知重点不在文学,而在历史,亦即在“历史大叙述的缝隙”和“繁琐与尘俗”的生活经验之间,做了一个重建现实中国的尝试。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另一著作《小说中国》 的英文名称是 Narrating China,他用 narrating(叙事)一词直接翻译“小说”二字,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不断出现的narrative(叙事),和grandnarrative(大叙事)的用语。他虽然早已告别了梁启超、鲁迅等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也不接受小说有救国责任的大话,但自别于“大人先生”而谦称“我生小辈”的他,在这里却俨然有追循西方叙事或大叙事的模样,再度展现了替中国现代文学开辟新天地的抱负,而他 《小说中国》 的架构也隐然具备了“大说中国”的庄严。事实上,他的《历史与怪兽》 一书的副标题“历史·暴力·叙事”也透明地证实了这个猜想。不过严格说来,把西方文学理论生吞活剥,不加修饰,依样画葫芦嫁移到中国,未免有声东击西,向声背实之讥;纵然满足了不少国人崇洋的心理,它与我们的国族主义有多少抵牾,在中国土地上能产生多少现实的意义,以及它可能得到的负面效应,王德威则未予深究,不免是他事业上一个致命的打击。

二
然而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和大叙事呢?大陆学者郑祥福用李欧塔(利奥塔)的话说:相对于科学而言,“叙事”的语言不需要任何外在合法性的支持,可以把无知、野蛮、偏见、迷信或任何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大叙事”则包含了当代因政治和哲学的推动而获得的新知。(郑祥福,《李欧塔》,台北生智出版,1995)依照李欧塔本人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是“人道思想的解放”,和“冥想知识的融汇”;当美学或抽象意识介入时,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哲学的,现实知识的话语,不再是如镜照影的复制,而是产生更多的话语,发现更多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透过文本,“从未知中求新知”。在讲求后现代精神的氛围中,没有比这样的陈述更具体有力了。如果说王德威在他历史的构想中有把小说变为大说,或者让小说接近叙事和大叙事的希冀,以便发现历史更多“千回百转”的面貌,确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经过这番努力,借重西方的文学知识,他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视野,而在我们历史和地理双重背景快速改变中,加上“华文”或“汉语”的新框架,把中国现代文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他功不可没,早已与“梁启超与鲁迅一辈”分道扬镳了。
然而王德威给人的印象还不止于此。跟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和大叙事遥相呼应的,还有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传统”。那是当年煊赫一时的“新批评”(NewCriticism)学派大师利维斯的创造。利维斯根据文学的模式,力排众议,替英国小说制定了一个从简·奥斯汀到D.H.劳伦斯的大传统,取舍之间,排斥了狄更斯、斯特恩、哈代这些卓具声望的作家,虽然一时惹起不少争议,却为当时正在耶鲁大学求学的夏志清拳拳服膺,希望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圈内做一点类似的回响。他毁誉参半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便是在这种氛围下完成的。王德威师承夏志清,十分理解其师追踪大西洋彼岸利维斯的心意:
利维斯认为,“他所选择的”这些作家既能发挥对生命的好奇,又能将其付诸坚实的文字表征。在《小说史》一书中,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 〈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夏志清的“大传统”肇始于他的“筛选”,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他贬低鲁迅,而对新文学的名家如茅盾、巴金、丁玲等,“也吝于给予过高的评价”。在 《小说史》的结论里,“他列举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四人为其中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现‘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尽管张爱玲和钱钟书“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史里,皆是默默无闻之辈”。
王德威对夏志清“开路工夫”的辩护,和“批评精神与信念”的推崇,尤其在夏辞世不及旬日的今天看来,慎终追远,是公允而适宜的;而他认为当今“许多年轻的批评者其实与夏颇有契合之处”,应当也包含了他自己,因为他们都“为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变与不变写下新章”,而他们所揭橥的大传统不过是“在在要引起我们的思辨”而已。王德威的努力,正是此一理念的薪传,值得褒扬。只是处于后现代思想全球化的新时代里,他接受了比夏志清更多的西方理论,淡化了他自己所提出“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意识———这些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喧哗”,难免要遭到“文化拼盘”和“挟洋以自重”(王德威,《西方理论视野下的现代中文小说研究》用语)的低贬了。事实上,在他的论述中,他于意识形态和文学现代性的认识,用力甚勤,然而忽略了台湾许地山、王祯和这一系列的乡土文人,或者大陆新生一代向历史告别、走出悲情的张炜等人,诚有沧海遗珠之憾。
文学创作的变与不变,不同于文学的批评,总是以人的感性为前提,没有历史系谱学的时间表,没有客观事实作为背景,也用不着批评家官用的印记。
然而说到文学的传统,不论是利维斯、艾略特,还是夏志清,重点都在历史,或者透过诠释而获得的历史再评估。过往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生命与经验的总和。如果把小说扩充为大说,把大叙事扩充为大传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历史,我们欣然回到了文本的怀抱。文本主义者最爱用的一句话,“语言之外,别无世界”,道破了文本和历史之间微妙的关系。的确,在嬉笑怒骂、感时忧国……等等的喧哗之后,虚构而成的小说,或者说出于记忆得来的书写,纵然支离破碎,仍然是血淋淋的历史。王德威在这种目的下广事搜罗,补苴罅漏,思考小说怎样见证和介入历史的问题,不斤斤计较于作品的良窳,不事杀伐臧否,确是后现代思想的精神,不应当有推石登山的困境。
但事实却不然。如果历史真的可以重建,尼采早已指出记忆的不足,历史残缺不全的必然性,以及被理解而归纳成知识后的历史往往是一个“死去了的”历史。他甚至指出当生活痛苦或不如意时,有人宁愿选择遗忘。在另一书中,他甚至相信人类在某些情况下,会为了需要和欲望而虚构现实。在这里,我们也不宜漠视蒙田更早的警告:人在折磨中所做的“坦白”,是不足为凭的。我无意指陈在动乱和政治干扰频繁年代中出现的作品,会有虚伪不实或者过分夸张之虞,但历史学家具备一点哲学家的慎思明辨和怀疑的精神,是有利而无弊的。伽达默尔同意人文大师狄尔泰对历史诠释学的看法,认为理念不应当做成历史哲学的核心,但他们仍然相信历史的研究终会“无可避免地”回到理念。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人自身理解的有限性就是实在、矛盾、荒谬和不可理解的,谁认真地看待这种有限性,他就必须认真地看待历史的实在。
不同于夏志清对美学的青睐,王德威对这里所谓“历史的实在”有相当的掌握。他不担心历史的片面性;他不以文学的“美学质素”做优先考虑;他接受生命中出现的一切现象,包含“现实、矛盾、荒谬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他的谴责小说、风月小说、政治小说、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无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他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文坛在这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中,却意外进入了一个繁华似锦,百花齐放,类似文艺复兴的大时代。然而事实上,小说在今天早已失去了时代的魅力,而有识之士,包括他自己,也都明白“这不再是一个阅读至上的时代”;且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人赋予“人”的浪漫形象,早已破坏无余,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权力的支配,和政治因素的夸张。这种西方文化的没落,和西方人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不能幸免,只是王德威在我们历史千变万化的的震撼中,把它搁置在一旁,别有用心地做了他认为更为重要的选择。

三
事实上,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最受到他瞩目的,不是全球性的颓丧,而是世纪末的乱象。这些在中国,不,根据他的定义,应当是两岸四地天天上演,日日登场的悲喜剧,例如疯狂与叛逆,革命与淫乱,寻根与乡愁,罪与罚……等等这些令人“目眩神迷”、不可掩饰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喧哗。
严格说来,他所强调的乱象,是人性丑陋一面的流露,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社会发生。他最爱引用的巴赫金式的狂欢,事实上跟我们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巴氏的理论,见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他认为陀氏的小说有四大特色,其中之二,便是人物的“无定论性”(unfinalizability),和“狂欢”(carnival)的介入。陀氏的人物,在巴赫金的眼中,是一场与外在世界连绵不断的对话,一如我们哲学观念中阴阳二元无休止的交叉与组合,永无定论之时;人戴上了未知的面纱,故事的发展也布下了未知的疑云。至于我们两岸四地的小说,感谢我们伟大历史传统阴魂不散的力量,不论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白薇的《打出幽灵塔》,还是阎连科的《受活》,这些在一出出“血泪”悲剧里出现的人物,从一登场,便挂上了黑白分明的脸谱,不容读者太多的幻想。这种简化人性的描写,与巴赫金多元化的生命观背道而驰;而在人道主义解放的今天,不唯失去了小说的深度,且不再有取信于人的力量。我们的文学应如何跳出此一泥淖,争取新的活力,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有宏观意识、也以文学前途为己任的文论家,王德威对此一问题的缄默,令人诧异。
至于陀氏的狂欢,无论王把它译为嘉年华,还是众声喧哗,也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想象,绝非大义灭亲、革命加恋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类大声镗嗒的呐喊可以相提并论。相反地,陀氏的狂欢,在巴赫金的认识中,是一个更偏向于个人内在的行为。人都有想从生命的约束或禁忌中解放出来的冲动,最好的例子便是《罪与罚》的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梦想成为拿破仑的一天。这种冲动不会锣鼓喧天,只是心灵中的鼓舞和默祷。王把这种观念运用在现代中国小说家的身上,未免离谱太远了。至于王德威和陈思和等人在阎连科《坚硬如水》一类“文革”小说中见到“革命加恋爱”那种魔鬼式的狂欢,应当溯源于巴赫金的另一著作,即论法国拉伯雷的荒谬现实一书。在这里,拉伯雷戏称为“吃喝玩乐”的嘉年华会,是名符其实的狂欢,是群众聚合在一起,饮酒纵欲,飞扬跋扈,而罔顾一切的时刻。这跟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疯癫确有近似之处。不过细观东西方生活和思想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拉伯雷的狂欢与我们的行为也并不沆瀣一气:西方人在节庆大典中戴上面具,穿上奇装异服,根据巴赫金的解释,是掩盖自己的脸孔、年龄、职业,以及社会地位,而以集体形态为幌子,忘记高贵与低下,道德与荒淫的悬殊,让自己在忘我和堕落中获得重生。反观我们“文革”时代的举动,以少数的特权阶级,利用政治势力的庇护,荒淫无度,作威作福,不可同日而语。不论王德威如何欣赏巴赫金的哲学,把巴赫金的哲学放在我们的社会里,显然方柄圆凿,格格不入。
事实上,王德威也感觉到这种张冠李戴的不当。他在《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收录于阎连科,《为人民服务》,台北麦田出版,2006)一文中舍弃了巴赫金,却换来了巴塔耶,一个解构主义运动中的法国小说家。他相信巴塔耶的理论更接近他的需求。的确,对巴塔耶而言,不唯色欲和境界可以彻底消融,在他的世界中,理性已全盘瓦解,剩下的只是属于生理上的肉体经验。他最著名的《眼睛的故事》是一部难以想象的情欲小说:一对热恋中的少年男女,杀害了教堂的神父,挖出他的眼睛后,把眼睛塞进少女的肛门和阴户里,藉以取乐。阎连科《坚硬如水》里的高爱军和夏红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炸死岳父之前,给绑在椅子上、封住了嘴巴的岳父,从容不迫地做了一场猥亵的春宫表演。在中国小说圈内,在中国人伦关系似断实存的社会中,这是一桩匪夷所思的大事。用理性来解释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阎连科自己“发明”的“神实主义”也派不上用场。一部当初人人都以为是低贱的“黄色小说”,奇迹似地跳出了它卑微的身影,在文学的天地里,取得崇高的地位。这正是文学不可思议的地方。
如果黄色小说的目的只在刺激人们的感官,并非难事;这类的商品从来便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必浪费评论家宝贵的时间。然而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兼顾的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这部严肃书中,王德威为当代情色小说花费了偌大的篇幅,真是洋洋洒洒,几乎打出了推销色情的招牌。其实如果他只想突显“小说怎样见证及介入历史”,他说得够多了。从文学的角度谈到文学作品时,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叶兆言的《花影》,他从不涉及艺术的优劣,境界的高下,只着眼于读者阅读时“爽与不爽”的感受,或者作者在书写疯狂的爱欲时,是否有“夸张”和“过瘾”的享受。至于台湾的作者更可笑了。例如自许为性学大师的曾阳晴,奇想连篇,幻想走进自己的肛门,经过肠胃,再从嘴巴出来,仿真大便回到肛门,而从嘴里吐出食物的过程,令人恶心。这个两百年前《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说过的笑话,放在他的手中,除了证明恋秽癖外,别无新意。
王德威对男性作家的失望,或许可从女性作家身上取得补偿。他开出一系列女性小说家的名单,例如袁琼琼,钟玲,萧飒,她们把性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给予尊重,的确胜过只求“爽到”的须眉多多。再如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不标榜情色,而情色自见,把感官和幻想结合为一,把欲望和绝望呵成一气,展现人们在生活中不同的心境,高下之分,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批作家,趁台湾解严后社会高度开放的自由,深入禁忌,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跃登畅销书的榜首。例如1997年的 《北港香炉人人插》,“引来人人奔走相告”的轰动,确是情色小说罕见的高峰,不唯震撼了作者李昂,还让王德威感慨地想到“小说到底是怎么写的”问题。(王德威,《性,丑闻,与美学政治》,见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序论,台北九歌出版)如果一部小说的本身受到质疑,小说家的身份还能成立吗?但这显然不是李昂个人的问题;王德威一再提到现代作家文字修养和技巧的欠缺,却从未做过严肃的批判,有违其师夏志清的教诲。他对“色胆包天”、“花样最怪”,而“文字装备不够精良”的曾阳晴,竟寄望有一天“写出二十一世纪的《肉蒲团》”(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令人大惑不解。王以《肉蒲团》为情色小说的高标,或许只是对传统小说口头上的尊敬,不足为怪,但《肉蒲团》文字的造诣和幽默感,自有它的长处,不是人人“好生将养”,一夕之间便可登其堂奥的。
如果我们无法把《肉蒲团》当做“觉后禅”看待,至少可以一笑置之。中国人对“爽”其实有优美的传统;“美酒饮将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越分和泛滥,从来不是上选。福柯在《性史》中推崇中国的“性艺术”,批判西方的“性科学”,让我们不禁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
然而好的小说,不论情色还是政治,严肃还是诙谐,都不是一蹴可就的。作家的涵养,作品的水平,在在需要经营和提升;文学史家眼中的“现代”或“后现代”这些历史性的名词,对作家并不重要。中国人对生命有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也有一向的尊敬。然而这二事是不容混淆的。王德威对现代华文文学史的关心,遍及两岸四地,任重而道远;而他奖掖后进,兼包并蓄,不事攻伐,亦不可多得。然而他的可议处,在虽然掌握了文学的历史,却疏忽了它的明天,也就是作为文学第一生命的“美学质素”。没有它,我们没有希望攀登艺术的高峰,成为世界文学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我们的写作,除了消遣,将别无意义。
王德威在言及台湾小说的创作时,提到一位“年轻的文化人詹宏志”,他感叹台湾文学如果频频处于政治、文化的干扰之间,它的努力“是否将成为一场‘徒然’的浪费”。撇开政治文化的议题不说,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家可以容忍曾阳晴、李昂文字上的缺陷,白薇、蒋光慈艺术上的失败,张大春写作上的懒惰,莫言、阎连科小说结构上的草率,而无不安之色,不仅台湾文学的努力将是一场浪费,华文文学向世界进军的梦想,恐怕也将成为“徒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如此疵瑕百出,漫无准则,而评论家却处之泰然,视若无睹的。
王德威在《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文中曾说:
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任务。
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希望也是他《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一书“大哉问”的严肃回答。文学的历史,是菁英历史,不是时代的流水账,更不是个人好恶的备忘录。如果文学史家能出入当代,放眼未来,发掘不朽的作品,辨别良窳,让玉石攸分,高卑有序,则我们华文文学走入世界的梦想,可计日而待了。
(作者系文学教授,曾执教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康奈尔大学)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