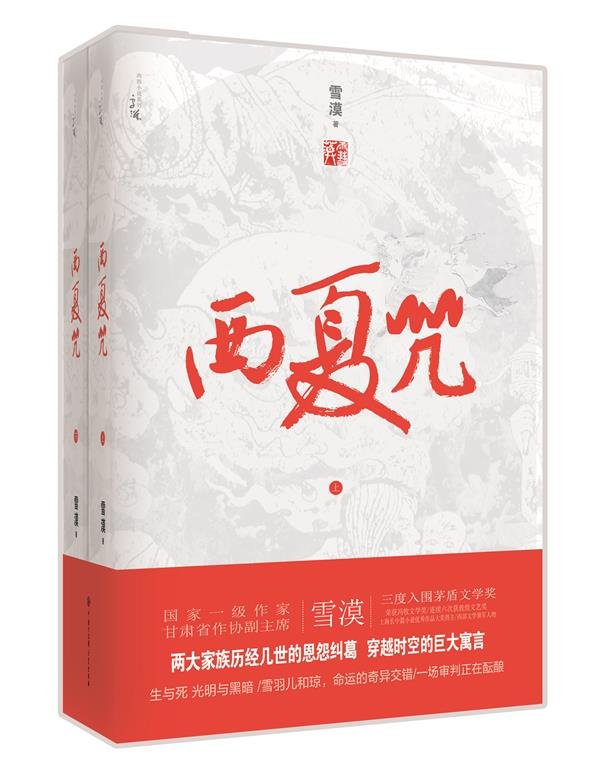
读《西夏咒》:唤醒被梦魇裹挟的灵魂
作者:听雨
张潮《幽梦影》有文: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乃地上之文章。
文章和山水虽同供人欣赏,但读者在其二者之间的体悟却因人而异。
读雪漠老师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人甘之若饴,有人以“逆行菩萨”的身份谓故弄玄虚。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一切都在于心,由天使到恶魔的转变只是心变了的缘故。
有人选择成为佛,就有人选择成为魔,还有人选择停留在梦魇的裹挟中随风飘荡。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了自己的心,任人摆布,终身都在为他人摇旗呐喊。
这些摇旗呐喊者,也许是你,是我,甚或你我都是。
不信的话,请打开《西夏咒》吧。
读之,从中便能找到你我的影子,而读之的目的则是为了能从梦魇的裹挟中惊醒,让灵魂醒来,让心得以安放并平静下来。
《西夏咒》是中国一级作家雪漠创作的长篇小说,曾获得了“第四届黄河文学奖”和“第七届敦煌文艺奖”。它和《西夏的沧狼》《无死的金刚心》一起,构成了作者的“灵魂三部曲”,也预示着他的作品从展示生活进入了灵魂求索,从现实世界进入了灵魂世界。
该小说通过对从西夏神秘岩窟/金刚亥母洞里发掘出的历史书稿的解读和演绎,展示了鲜为人知的西部人文景观。
主要描绘了金刚家和明王家为水源而进行的争斗,以及琼、雪羽儿、阿甲等人物不同的精神求索。
雪漠老师在东方网的访谈中讲道:人在兽性之外还有着神性。所谓的神性,你可以理解为人有更高的追求。除了谋求生存的那种动物性之外,人还追求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即信仰,即琼、雪羽儿、阿甲所追求的。
一,无信仰的人终害人害己
小说中的谝子,是没有信仰的,他既不崇拜也不认为有。
早年喜走狗放鹰,使枪弄棒,枪法惊人且记忆力强的他,以一流的口才和权术,以及暴力手段,成为了金刚家族中权势显赫的族长。
他带领另外一班没有信仰却有着奴性的人,在大地上飞驰。认为除了天,他就是金刚家老大,无畏无惧。
在饥荒年代,空中到处“响彻”着饿死鬼的哭声。饥饿已成为历史梦魇。金刚家已饿殍遍野。
阿番婆天天睁着猩红的眼睛,待在村口盼儿归。没法,等不回儿子,来村子里求生的路人,便成了她地窖里的冤魂,因为饿呀。
人吃人,就连雪羽儿也吃惊,舅妈也想在深夜里吃了她,就像《深夜的蚕豆声》中描述的那样。
谝子为了金刚家的“面子”放着储备粮不用,却把前来“偷”粮救人的雪羽儿“砸断了腿”,并流放到王景寨戈壁滩放羊。后,雪羽儿妈被村里人煮食。
在金刚家与明王家的争斗中,谝子的选择是不择手段。
先是威逼利诱瘸拐大,把他老母亲抛入水中,活活砍死,从而嫁祸给了明王家。
其后,在骑木驴“争斗”中,谝子以“破鞋”罪名对雪羽儿妈进行惩罚,引起其他村子纷纷效仿。自觉金刚家的女人无胜算,便利用“天女”优势,虽在众多骑木驴的女人中赢得头彩,却引发了骚乱,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这骚乱,骚动的是男人女人们的欲,乱的是人的心和性。
这种毫无人性又冷漠的行为,是在为谁摇旗呐喊,又是在为谁充当着牺牲品。鲁迅文章中的“人血馒头”在眼前显现,人性中的恶与愚无限放大。而谝子成了暴力本身。
他算计了天,算计了地,算计了同伙,算计了草民百姓,唯独没算计到的是他的死。
最后,他的小儿子摔断了他的脊梁骨,多年之后像一条死狗,连同他惯于狰狞的面孔和所有恶行一起被儿子们埋入土坑,成为他唯一活过的证据。
二,被命运裹挟着的人,灵魂犹如无所依的气球
《西夏咒》中写着: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选择,俗事里泡多了,灵魂就成了无所依的气球,忽悠悠晃,无着无落。
小说中的宽三、瘸拐大及其他带有奴性的人,就是这无所依的气球,被命运裹挟着、困在自己的魔咒中走不出来。
宽三,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跟着谝子做打手,力大如穷,擅长掌掴。
在谝子的“英雄”事迹里,几乎都有宽三的身影。他的心让猪油蒙着,没有黑透,只是未觉醒。
因为在雪羽儿被谝子抓住时,曾想救雪羽儿远走高飞,他的心中还存有善念。
还因为在大饥饿时期,宽三策划了“鸡毛传贴”事件,救助村人度过难关。
最后因为忏悔,改变了村人对他的印象,得到善终。
瘸拐大,大孝子,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擅长做皮货,金刚家专职驮水。
在家府祠驮水,能给妈时不时烧个山药,也是他平日里在谝子面前猫腰塌背的功劳。
平日里,他像根草绳,叫人用脚搓来搓去,宽三见他跟见了牛粪一样,今儿却满脸堆笑地和他打招呼,瘸拐大膝盖股一软,差点儿跪了磕头。
宽三和他打招呼,是来传达谝子命令的,令他把母抛入水中送死以栽赃于明王家。
谝子叫谁死,谁就不能活,尽管瘸拐大在背后问候过谝子祖宗千百遍,但当着谝子的面时,他仍然习惯性的猫下了腰。
从此,瘸拐大母亲便成了坝上垒起来的那堆石头里的白骨。
瘸拐大便时常想起那白骨落泪。白天想,夜晚想,心里有苦的时候更想……
想妈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骂宽三。驮水的时候经过那石垒,听到妈叫“香娃子”,他就毛骨悚然,于是心里念叨,让妈别怨他,他也是上了弓的箭呀。
“历史的巨眼是忽略一般人的。没人去关注一个百姓的心事,虽然那内心的激烈程度不弱于一场战争,但历史却只记得战争,并将战争的制造者当成了英雄。”
既可怜又可悲的灵魂,只能是任人摆布,心里布满了灰尘,眼里满是悲哀。
尽管灵魂找不着出口,能活还是得活下去。只是瘸拐大命数也到了尽头。
为上头做法器时,被明王家拉入地窖,传授活剥“皮子”绝活。一个月后,他成了黄泉路上的孤魂,他哼着一支忧伤的调子,气球般游荡在通往地狱的路上。 他还依稀记得,他曾干过多少伟大而辉煌的事呀,做木撅,遛皮子,都是叫祖宗长脸的事。当然,他也记起背母亲往河里扔的事,于是他哭了,哭的撕心裂肺。
三,凤凰涅盘
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没有哪一位成员可以逃脱命运的“裹挟”,任何事物,自打存在的那一刻起,就无法摆脱命运的大网。
正如作者诗里写的:
我一次次死去,一次次再生
扮演着眼花缭乱的角色
生生死死,无休无止
忽而牛,忽而马,忽而猪
可无法摆脱命运的磨盘
没人能告诉我
哪儿是灵魂的出路。
琼进入梦魇,枣红马也梦魇着。见马望他,琼拍拍了马脖子,说,我活着时,摆不脱梦魇,当肉体消失时,那梦魇也结束不了,我这是灵魂的梦魇,你那只是肉体的。
琼的内心里渴求“光明”和“真理”。他不甘心困在灵魂的桎梏中,他和阿甲,雪羽儿一样,是腐尸虫眼中的异类,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
书中的琼有时是谝子的儿子,有时是那个来朝圣的僧人,几条不同的线索交织着构成了此书。
琼就是在这样的梦中互换着角色,但他的行为从来没离开过向往与追求。
就像阿甲常说的:“不修行,想不出活着的意义。修行,想不出修的意义。”“守住你的高贵,坚守你的孤独,走你自己的路,灵魂无主者,才是真正的难民。”
在《梦魇》中,琼是谝子的儿子,谝子想方设法让琼随他,成为一个强盗,而琼的妈妈和舅舅(吴和尚)却一直希望他能出家,能去朝圣。后来,琼真的成为了僧人,只是他的妈妈要每天挨谝子五十鞭子,舅舅给谝子当了马墩。
在他的身边,当每一宗罪行发生的时候,他哭泣,内心在咆哮、呐喊,虽然唤不醒被梦魇裹挟着的灵魂,但他毕竟尽力了,那种痛直渗入进他的灵魂。
他不清楚自己那天在宽三的眼皮底下是否和天女有染,破戒那可不是他内心想要的;他不知道金刚家人为什么要惩罚有恩于他们的雪羽儿,那么残忍、冷漠地吃雪羽儿妈;到处都是孤魂野鬼唧哇乱叫,哪里才能找到清凉之地,澄明之境?
带着这些迷惑和寻觅,他和雪羽儿一起双修,最终,超脱了梦一般的红尘对他的束缚和历练,打碎自己的执念,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
雪羽儿,小说中的空行母,凉州飞贼,奶格玛的化身,是光明大手印瑜伽行者。
“雪羽儿每次对妈的追忆,都是扎向她心头的钢刀,身不由己像下山的石头滚进这个巨大的泥潭。泥潭深不可测,没人知道有多深,只有难以言说的恐惧。自妈懂事起,天就露出残酷模样,那是块铁板,是溢出寒霜的残酷,是不容分辨的专制,像毛风一样呜呜地罩住了她们。”
这段话,是雪羽儿在她和妈经历了极端痛苦的若干事之后,内心的独白。
一切恍若梦一般。
她的命运始终被某种力量裹挟着,身不由己地干一些自己也未必愿干的事。
她在尘世唯一的的牵挂只有妈,后来妈没了,她不得不放下了。
放下之后,她远离了愚痴、贪婪和仇恨,一步步走近了清凉,和琼一起成为了双修伴侣,明白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永恒”即利众。
利众的人,其过程注定是孤独的。
一个天大地大的岩窟里,要寻觅能拯救人类的牛蹄窝里的水是多么孤独,只要灵魂里有那粒种子,它长呀长,总有一天,就会参天的。那本该你拾到的水,正在天地间的某个所在,朝你偷偷地笑呢。
结语:
雪漠老师对遥远西夏历史中金刚家的记述与描写,实则也是对人性描写和对现实的批判。在善于恶的争斗中,善终于超脱打碎了恶的世界。
世间无永恒,我们都是被命运裹挟着来世间的过客而已。肉体消失,命即消失。修行的意义就在于,升华人格,重铸灵魂,就可能有精神层面的的相对永恒。
雪漠老师的《西夏咒》,是老师的“附体的写作”,其内涵丰富,激情饱满。涵盖了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宗教的信仰、生与死的困苦、坚韧与虚无,时间的相对性等等。
如此多的内容涉猎,显然是当代小说所没有的,实属一部带有悲悯情怀的奇书。
《西夏咒》是一部透过死亡看生存,透过人物看文化的悲悯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