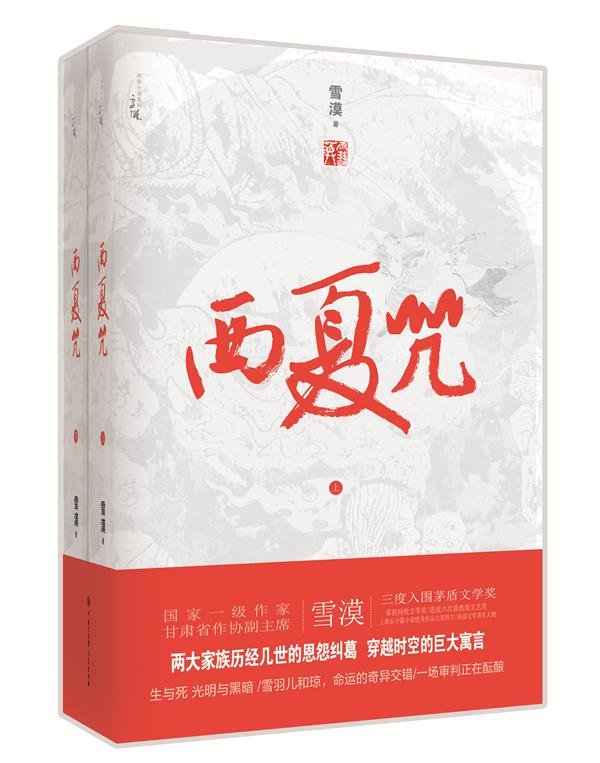
西部的现代性——论雪漠小说(二)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异域里的灵异:附体的写作
文学的地域化特色一直很可疑地在文学史叙述的边缘地带徘徊,它总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欠大气的艺术特色得到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实际上早已是一桩不明不白的案件。中国革命文学席卷了乡土文学,也可以说是在乡土文学这里找到了它的寄宿体,结果显然就像所有的宿主最终变成了寄生者的营养资源一样,乡土文学也成了革命文学的营养资源。这也是中国革命文学得以成功的地方所在。中国的革命文学力图反抗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它无法凭空创造一个更新的宿体,它只有寄生在比资产阶级文学更加“落后”的农村/乡土身上,来创建革命文学。这本来是(可能会是)一个奇妙的结合,但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力量过于强大,几乎压垮了中国乡土的本真经验。那些乡土、地域性特色,都只是主流革命叙事在艺术上的补充,经常还是勉为其难的补充。但直到历史宏大叙事面临解体危机,人们才如梦初醒,文学单靠意识形态的机制来生产是难以为继的。转而文化成为一种更为靠近文学本身的资源。80年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小说已经难以花样翻新,尽管后现代的文学也是以反抗资产阶级艺术自律为任务,但仅仅依靠语言的反抗远远不够,也难以有持续的力量。文学还是要回到历史的可还原的情境中,才可能找到更有力的支撑。故而80年代的拉美文学受到了追捧,那种文化已经是在“前现代”的异域神奇上面做足了功夫了。以至于魔幻色彩可以点铁成金,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望尘莫及。
实际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不管是鲁尔夫、马尔克斯、略萨,还是博尔赫斯、萨朗等人,他们都深受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文学观念和小说方法方面,他们都属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体系。只是南美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尤其是神秘的玛雅文化给予他们的作品注入了“前现代”的神奇灵性。中国西部的作品却是以更加朴素的生活原生态的形式仿佛回到现代之前的原始荒蛮状态,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其艺术表现方法比较粗拙,但那种生活的质地却挣脱了现代性惯常的历史理性以及观念性,当代中国文学更为本真地回到生活和生命本身。雪漠作为一个西部作家,并不是直接把日常经验临摹进作品,而是站在西部的大地上,激活了西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甚至是那些传统和神灵,以及那种来自大地的气息。雪漠的西部书写几乎是遵循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回到“前现代”,反倒是以最为真切的方式打开了这一片异域天地,当代中国文学在正视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时刻,也获得了它坚韧存在的理由,并因此成为世界文学的异质性的“另一部分”。
西部作家并非因为他们处于贫困落后的生存状态而去控诉现代化,就其文学书写而言,他们实实在在地享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并且有着西部文化的自信。贾平凹从90年代更深地回到他的西北文化,以传统与民间重新构筑他的文学底蕴。《秦腔》开始,就可以看到他彻底回到乡土的那种自信和自觉,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例如《远山野情》《鸡洼窝里的人家》《商州纪事》等,西北的生活包含着风土民情,自有一种疏朗和俊逸,人性的温暖偶尔散落其间,更添一种意味。《废都》风格上向着古典美文如《西厢记》《金瓶梅》靠拢,却只是保留了西北性情的神韵,实则是在生活情状方面疏离了西部的荒蛮。《废都》遭遇到阻击,他或许痛定思痛,干脆转向了更加纯粹的乡土。我们在《秦腔》里可以看到,贾平凹干脆掉到泥地上,他宁可用他的身子贴在乡村的土地上写,也不站着把目光投向虚空灵动的乡村“性情”——尽管那曾经是他最为拿手出色的技俩。《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极花》之后,贾平凹回归乡村的写作,越来越彻底,越来越随性,也越来越自由,这得益于他的更单纯、更自然地回到乡村的大地上。他去写作生活本身,写作人本身。所有这些前提,都表明中国文学不可避免从历史走向文化,并且要在文化中打开一条更加彻底的通道,在那里去触及他们理解的乡村中国的生活内在性,那种生活的质感。同样生活于大西北的雪漠,甚至更西、更北、更荒芜的雪漠,他握住的生活的原生质地,并且从这里再度掘进,他去触及生命经验中更异质的经验,在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神灵和鬼魂,它们不只是偶尔闪现,充当技术的或形式的装置,而是经常在场,在小说叙事中起到内在意蕴构成的作用,当然也起到叙述引导的作用。在历史退场之后,在“反思性”消解之后,他的写作却引向了“逆现代性”的路径。
雪漠在西域生活的荒蛮状态中找到他的文学表达,随着雪漠的宗教经验的积累和领悟,他对生命存在之不可洞悉的深度有更敏锐体验,并且寻求文化形式表现出来。2011年,雪漠出版《西夏咒》,这部作品就显示出雪漠相当大胆的探索,他所表现出来的反常规的方法,与其说是在呼应先锋小说当年的形式实验,不如说是他自己对西部异域历史的探究所致,也是他浸淫禅宗“大手印”法门的文学感悟,因而,他有胆略和能力把历史、文化、自然、生命与神灵混为一体来建立他的文学世界,看上去是在冒险重构“怪力乱神”路数,但也是对汉语文学的异质性经验的强行探索。
雪漠此前的几部小说的主题以悲苦基调;追求持续性的故事发展的张力结构;情节设置追求完整性;粗砺和硬实则是其美学上的显著特点。但《西夏咒》却是要开辟出另一条路数,小说叙述显得相当自由,甚至十分灵活多变。尽管说小说有不少的细节、段落和句子还值得推敲,有些写法似乎还欠妥当,打磨得还很不够。但这部小说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其新不是因为假托发现古代遗本;也不仅仅是随意变换的叙述角度和人称。最为重要的,是其内在推动机制,内里有一种无法驯服的灵异冲动在暗地使劲,表现在文本叙述上,就是如同神灵附体,使得小说叙述可以如此沉浸于那种情境,如此无所顾忌切近存在的极限。灵异冲动使得西部长篇小说对文化关切发生质的改变,贴近历史、大地和文化,现在变成贴紧事相本身,使事相本身具有灵性。写作就变成神灵附体,叙述就是被神灵附体,仿佛就是神灵在写。由此才生发出小说文本的自由多变的结构和无拘无束的修辞性表述。当年最早由孙甘露在《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尝试过,后来又由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以及《一腔废话》更极端地实验过的修辞性表述策略,在先锋派那里是语言的修辞机能引发的延异游戏,在雪漠这里却是一种本体论式的灵知写作,其背后有个不得不说、不得不如此说的叙述人。雪漠有他开掘的灵知资源,有他几十年代的灵修做底,进入这个领域他仿佛摆脱了现世的羁绊:
因为抛弃了熟悉的笔法,他再也写不出一篇文章;因为有了新的文学观,他不再有满意的素材。他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为了摆脱扰心的烦恼,雪漠开始每日禅修,并按苦行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饭后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雪漠过午不食,并坚决地戒了与他相依为命的莫合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
坐禅之余,他形疲神凝,恍惚终日,昼里梦里,都在练笔。
终于有一天,雪漠豁然大悟。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他说他从此“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成功”的执著。奇怪的是,这时反倒文如泉涌了。他明白,能重写《大漠祭》了。
据说在1993年雪漠30岁生日那天,他剃光了头发和胡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的4年。他的创作进入宁静和超然,笔下的“人物”自然成形,文字从笔下自然“流”出,似有神助。这些说法,可见诸报端,也有笔者多次与雪漠交谈所印证,雪漠笃信他的写作是突然开悟。
《大漠祭》还是以现实主义方法作底,也以大量西部现实生活作为素材,只是雪漠的叙述进入自由的状态,《白虎关》显然也还是由叙述人控制整体的叙述;但《西夏咒》的叙述却几乎进入迷狂状态,被一股自发的力量任性地推动。这部作品可能会让大多数读者摸不着头脑,但只要读进去,这部作品无疑是具有过硬的内涵品质的作品。如此多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与死的困苦、坚韧与虚无、时间之相对与永恒等等,这部名为小说的作品居然涉及到这么多的观念,这显然是当代小说的一部奇书,可能小说这样的概念都要随之变化,至少对我们当今小说的美学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派探索在90年代已经转换,或者沉寂,或者隐蔽而为更为内在的经验表现。在小说形式方面做激进探索的文本越来越少,而能做到令人信服的文本实验则更少。因为,今天的形式变化可能是更为复杂的探索,需要更加充分的知识准备和极其独特的经验发掘。也正因为此,在西北凉州的雪漠,却以他独有的灵知感悟,如此任意而又自然的方式,开辟出小说的自由形式,提示了汉语小说拓展别样路径。
到了《西夏咒》,雪漠试图把西部的灵异思维与小说的文本建制结合起来。这部小说采用了多文本的叙事策略,它由几个意外发现的古代遗稿拼贴而成。它自称来自几个汉子修筑洞窟在土堆里发现总名为《西夏咒》的书稿,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成的书稿有八部,小说的叙事就是不断揉合这八部遗作而展开。小说借用原遗稿的《梦魇》《阿甲呓语》《遗事历鉴》等几部展开叙事,文本的展开显得相当灵活自由。小说一直是在与人谈论或介绍这几本书,就是说,叙事是一种转述,也以转述的方式借用了所谓“遗稿”的风格。这样,小说就自然地进入了风格怪异的叙述,飘忽不定的、迷醉般的、魔幻的叙述,各个文本之间的转承,也如同碎片的拼贴,也由此自然地切入那些异质性的极端经验。
《西夏咒》以其极端怪异的笔法,它要写出一个受尽磨难的西夏,那里容纳了那么多的对善良的渴望,对平安的祈求,但却是被罪恶、丑陋、阴险、凶残所覆盖。历史如同碎片涌溢出来,那个叙述人,或者阿甲,或者雪漠,只有如幽灵一般去俯视那样的大地,去追踪那些无尽的亡灵,去审视掂量那些大悲大恸之事相。写作如同神灵附体——那是阿甲、琼或是什么一直未显身、未给出名分的哪个魂灵附着他的身体上。如此附体的写作才有灵知通感,才有他在时空中的穿越,才有文本如此随心所欲的穿插拼贴,才有文本的自由变异与表演。
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导向对人丧失尊严的痛惜与对权力和暴力滥用的控诉,使得这部作品的主题显出了坚硬和深刻,也正因为此,雪漠不惜把他所有的描写和叙述推向生命的极限状态。雪漠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杀生和污辱生命的诅咒,他以“宿命通”的报业作为他叙述的精神依据,一方面,那些恶障一定要现身,一定要以行为力量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作恶多端必会遭报应。这一切都是在雪漠体验到的灵知通感里展开并完成的,包含着他对恶的历史的严厉拒绝。
——《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68期
(待续)
【回放】雪煮《道德经》系列讲座(扫码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