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北京的文坛,有一个“四大名编”的说法,指的是四位老编辑: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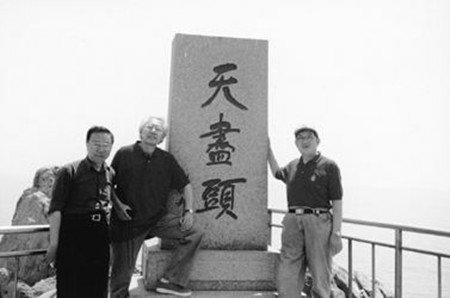
张守仁、崔道怡、章仲锷(从左至右)在山东荣城
“四大名编”轶事:编辑们的职业榜样!
文\孙晶岩
在北京的文坛,有一个“四大名编”的说法,指的是四位老编辑: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甘为他人作嫁衣
龙世辉我没见过,只听说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担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湖南苗族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了曲波寄来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作为一个资深编辑,龙世辉一眼就看出作品的先天不足:小说在语言结构上存在不少问题,文学性不强,严格地讲只是一堆素材。可他又敏锐地发现这个题材很棒,作者的生活底子厚实,有改写的基础。他热情地邀请作者来北京,和他一道商量如何修改书稿。
曲波如约而至,龙世辉苦口婆心地向他讲如何结构文章,如何剪裁取舍。曲波很虚心,说您是大编辑,我听您的。原稿中没有对爱情的描写,龙世辉觉得一部长篇小说全都是男子汉打仗不容易吸引读者,便别出心裁进行了新的艺术构思,他把自己的构思告诉曲波,但编辑的想法真要转化为作者优美的文字并非一日之功,龙世辉索性亲自动笔修改,呕心沥血几乎把小说重新改写了一遍,其中小白鸽白茹这个人物就是他加上的,“少剑波雪夜萌情心”等情节大大丰富了原著的内容。《林海雪原》出版后,作者一举成名。
没想到那个年代的人脑袋里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有人指责这本书里的“少剑波雪夜萌情心”等章节有小资味儿,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作者说这些内容不是我的原创,是编辑后加的。龙世辉因此遭到批评,背了个处分。
周围的同事都为这个朴实的苗族编辑打抱不平,可他毫无怨言。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王任叔(巴人)曾担任中国驻**大使,见多识广,知人善任。他对龙世辉充满同情,虽然社里迫于压力给龙世辉一个处分,可王社长居然在调级中一次性给龙世辉连升三级。他是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一种特殊方式给一个敬业的编辑以最大的支持。
龙世辉没有辜负社长对自己的厚爱,他编辑了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莫应丰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其中《青春之歌》成了风靡大江南北的畅销书,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芙蓉镇》和《将军吟》荣获茅盾文学奖。龙世辉殚精竭虑,用自己的才华扶持起了一个又一个作者,自己却清贫寂寞地告别了人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龙世辉就没有《林海雪原》。
磨稿斋中的欢喜泪
四大名编中的其他三位名编,我都有幸结识。章仲锷生于湖南,长于山东,既有湘人的古道热肠,也有鲁人的憨厚朴实。我上大学时,他来军艺讲过课。十五年前,我从青藏线采访归来,写出了讴歌青藏线军人的中篇报告文学《昆仑白雪》。当我冒着漫天飞雪把拙作送到《中国作家》杂志时,章仲锷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问我作品表现的是什么?我滔滔不绝向他讲述了那些主人公。其中有一个获得国际摄影大奖的昆仑山上的大兵贺凤龙引起了他的兴趣。我把贺凤龙拍摄的照片拿给他看,告诉他作者是个顶着高粱花子长大的农村娃,参军后凭着顽强的毅力刻苦地学习文化,执著地摸索摄影,成绩斐然。他听后很受感动,端详着照片对我说:“我们先看稿子,如果你的稿子写得好,我想把这张获奖照片刊登在《中国作家》的封二上。”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编辑部,没想到几天之后陈新增编辑就给我打电话说:“孙晶岩,你的稿子我们决定用,我和章仲锷、高洪波一起商量把你文章的题目改成了《白雪昆仑》,你看行不行?”我攥着话筒喊道:“太好了,《昆仑白雪》和《白雪昆仑》,虽然只是颠倒了名词的位置,但《白雪昆仑》比《昆仑白雪》叫得响。最后一个字用第二声念起来也更好听。”
章仲锷为什么对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兵这么感兴趣呢?原来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一九四八年,十四岁的章仲锷参军来到山东兵团随营干部学校,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到三野第七兵团政治部报社印刷厂当排字工。后来又担任校对、宣传干事等职,长期与文字打交道,他对错别字特别敏感,像啄木鸟吃虫子那样见到错别字就吃掉。后来,印刷厂的人集体转业,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像钉子似地挤时间学习文化知识,虽然入伍前他仅有初一文化水平,却终于在工作十三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从《十月》杂志的普通编辑到《当代》杂志副主编,从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到《中国作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他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为他人做嫁衣裳,不知培养了多少作家。
章仲锷家是一个文化之家,夫人高桦、女儿章则都在报刊杂志工作。一天,高桦老师约我到家里送稿子,她把我领进书房,我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块宽两尺半、高一尺的棕色木匾,上面刻着书法家董寿平写的三个绿色的大字“磨稿斋”。我顿时被深深地吸引了,磨稿,多好的斋名啊。一个磨字,渗透着主人对作者的厚爱,体现了主人对文学的忠诚。我问章仲锷斋名的出处,他说《当代》的主编秦兆阳曾经赠送给他条幅:“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他觉得这首拟自《红楼梦》的诗写得很有味道,就把自己的书房起名为磨稿斋。
章仲锷的书桌上放着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翻得都毛了边。他的案头功夫很过硬,错别字只要到了他的面前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他追求完美,遣词造句煞费苦心,编辑文章逐字推敲。理由的报告文学《痴情》、从维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张贤亮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土牢情话》、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刘心武的中篇小说《如意》、《立体交叉桥》、长篇小说《钟鼓楼》、刘白羽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谌容的中篇小说《太子村的秘密》、朱春雨的中篇小说《沙海绿荫》、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焦祖尧的长篇小说《跋涉者》……都是他亲手编辑打磨首发在刊物上的。
在《当代》杂志工作时,一个陌生的叫作王朔的人寄来了中篇小说《空中小姐》,编辑部副主任龙世辉觉得作者很有艺术才华,但小说写得太冗长,就约他到编辑部谈稿,提了一次修改意见后,龙世辉就调到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临行前把这篇稿子交到章仲锷手里。章仲锷看了稿子后很惊喜,他觉得这个作者最大的优点是语言独特,他对北京胡同串子的语言信手拈来,对军队大院小青年们的心态了如指掌。
章仲锷约王朔来编辑部谈稿,那时候的王朔显得很腼腆,接人待物彬彬有礼,尊重长辈,说话也是轻声慢语的。章仲锷一连找他谈了三次,说你的小说写得很纯情,但水分太多,要使劲压缩,去粗取精。王朔按照章仲锷的意见认认真真地修改了四遍,硬是把九万字的稿子精炼成四万字。章仲锷把王朔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在《当代》杂志推出了,小说写的是一个海军战士和空中小姐的爱情,既纯情又富有理想主义,很快就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紧接着,章仲锷又在同年发表了王朔的另一个中篇《浮出海面》,后来这个中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轮回》。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一年能在大刊物上发两个中篇实属罕见,从此,读者认识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王朔。
章仲锷看王朔创作状态不错,鼓励他再接再厉。王朔受到鼓励一发而不可收,一口气写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顽主》、《我是你爸爸》等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又是章仲锷帮他出版的。这些小说描写市井生活,其中有对伪道学的嘲笑,对旧秩序的颠覆。章仲锷又为王朔出版了《王朔谐趣小说集》。有人对章仲锷提出置疑,说他支持“痞子文学”,他斩钉截铁地说:“王朔一个普通作家的作品在一年内改编成四部电影,今年被称为‘王朔年’,中国哪个作家能做到这点?他的成名值得思考。”
一九八四年冬天,章仲锷到山西太原找焦祖尧谈小说《跋涉者》的修改意见,他先到了山西原平县找成一,又到太原附近的榆次找郑义和柯云路。郑义是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和史铁生、张承志等优秀作家是中学校友,从北京来山西农村插队。章仲锷来到郑义家,看到他家徒四壁,穷困不堪。郑义给了章仲锷一部中篇小说《远村》,告诉他这篇作品已经被六个刊物退稿。章仲锷看了小说,深深地被内容所吸引。小说写的是山西边远山村妇女“拉帮套”的婚俗。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小说描写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及一只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山西农村妇女因为生活所迫,委身于两个男人。她嫁给的那个男人是正式的丈夫,另一个羊倌是非正式的男人,这个男人和她的丈夫双方达成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这个女人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经济原因做出的无奈选择。章仲锷六十年代在京郊密云县搞“四清”时,见到过这种畸形的婚姻状况,所以对郑义的描写有真切的了解。他觉得这篇小说的人物写得非常生动,那条狗也写得活灵活现。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反映出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农村的贫穷。他担心《当代》主编孟伟哉不同意发,就写了几千字的审读意见交给孟伟哉。孟伟哉认真地看了稿子和章仲锷写的审读意见,拍板同意刊登。为了不惹人注目,排的小号字——万万没有想到,《远村》这篇不受人待见的小说,居然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章仲锷的山西之行满载而归,他发现了几颗文坛新星。《远村》的成功使郑义增强了信心,他又写了个中篇小说《老井》,依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题材,活灵活现的生活场景。章仲锷兴致勃勃地在一九八五年的《当代》杂志搞山西作家中篇小说专号,隆重推出了郑义的《老井》、李锐的《红房子》、成一的《云中河》、罗雪珂的《女人的力量》。还热情洋溢地以“晋军崛起,引人注目”为题写了编者按,“晋军”的冠名为文坛所认可。这期的《当代》在文坛引起轰动,《老井》被搬上银幕,获得电影国际大奖。张艺谋也因这部作品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一九七六年夏天,章仲锷发现办公室门后有个鼓鼓囊囊的布口袋,便问同事是啥东西?同事说是稿子。他问谁的稿子,看了没有?有人哼了一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别人无意说,他却有心听。这一口袋稿子得写多长时间啊,哪个作家会写一口袋败絮呢?即使真的是败絮,人家作家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多,咱当编辑的总不能连看都不认真看就给人家宣判死刑吧?征得领导同意后,他把稿子背回了家中,点灯熬油地翻阅着。作者叫王树梁,书稿的题目是《山林支队》,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晋北地区抗战的故事。他觉得稿子题材不错,作者也有生活,但作者显然不是搞文学的,既不会剪裁,也不懂结构。稿子整整写了一百五十万字,全是手写的,作者要花费多大心血啊!他给作者写了封信,约他来编辑部谈修改意见。
万万没有想到,王树梁是个下肢瘫痪的卧床病人,腰以下失去知觉,大便需要灌肠,小便要靠膀胱造瘘,生活根本无法自理。善良的章仲锷动了恻隐之心,亲自赶到医院看望王树梁。他刚走进病房,就看到王树梁正坐在病床上一个特制的木架里,胸前平铺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夹着一个小台灯,床前放着一个玻璃瓶,一根橡胶管从他的腹部穿出,黄色的尿液一滴滴流向玻璃瓶。
看到这个情景,章仲锷不由得眼眶湿润起来。创作一百五十万字的作品对于健康人都不易,对于残疾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这哪里是一个普通作者,这分明是现代的保尔·柯察金啊!他本来打算将修改意见详细地告诉作者,让作者自己动手改。可当他看到王树梁本人后,打消了这个念头。章仲锷觉得自己当过兵,熟悉山西的风土人情。自己是吃文学这碗饭的,改这篇作品有把握。面对王树梁这样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自己只能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他修改稿子,否则就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盛夏,章仲锷趴在斗室里辛勤地为他人做嫁衣。祸不单行,唐山大地震爆发,家家户户都不敢在家里住了。章仲锷家在故宫的筒子河畔搭起了防震棚,塑料布和油毡组建的防震棚白天闷热无比,晚上蚊虫肆虐,章仲锷心无旁骛,潜心耕耘着。他汗流浃背地写一段,就念给妻子和女儿听一段。为了使细节生动准确,他每个礼拜都要跑到医院与作者交流。经过一个夏天的认真修改,他终于将一口袋书稿压缩改写为八十万字,分上下两卷出版。书的封面赫然醒目:作者:王树梁。
《山林支队》出版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王树梁手捧《山林支队》,泪如泉涌。只有他才晓得在这部砖头厚的著作中,章仲锷付出了多少心血。人们纷纷给王树梁写信,把他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相提并论。在章仲锷的支持下,王树梁又写出了《千山万壑》、《鏖战平原》等佳作。章仲锷不仅帮助王树梁出版了书籍,更重要的是用文学激活了王树梁的灵魂,增添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当编辑就要磨稿,正是这个磨字,使章仲锷把一个个无名小辈培养成了闻名遐迩的作家,把一篇篇不成熟的初稿磨成了文坛公认的佳作。经过他的编辑,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郑义的《远村》、朱春雨的《沙海绿荫》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刘心武的《钟鼓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荣获茅盾文学奖。他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做人梯,托起了一个个作家,留给自己的却是高度的近视,严重的胃病,瘦弱的身体,春蚕吐丝丝不断,留取美文照汗青。
文学新秀的摆渡人
崔道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一九五六年,二十二岁的崔道怡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当时,恰逢《人民文学》杂志的繁荣期,王蒙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望着血气方刚的崔道怡,《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开玩笑说咱们编辑部也来了个年轻人。
刚一上任,他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李国文。李国文当时是铁路文工团的业余作者,一口气写了六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崔道怡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就给李国文写信热情肯定了他的作品,并约他来编辑部见面。李国文接到信激动万分,马不停蹄赶到《人民文学》杂志。崔道怡对他说:“这六篇小说写得都不错,但《改选》写得最好。你修改一下,我先发这篇,往后再慢慢发那些。”
李国文按照崔道怡提出的意见修改了小说,《改选》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从此,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直到现在,李国文仍然保存着崔道怡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崔道怡开玩笑说:“国文,把我的信还给我吧,怎么说我也是原创啊。”
李国文说:“我复印一份给你,原件我要永远珍藏。你知道一个名牌杂志的大编辑给一个小小的业余作者写信意味着什么,你是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啊!”
一九六二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他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不仅题目充满诗意,而且内容很有味道。他及时把小说上报主编,编发时还提出请画家黄永玉为之插图。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十八年后,汪曾祺又写出小说《受戒》,崔道怡激动万分,称之为可以传世的精品。由于种种原因,这篇作品未能获奖,崔道怡便将《受戒》收进自己编辑的“获奖以外佳作选本”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汪曾祺。汪曾祺不负众望,很快又写出了佳作《大淖记事》,荣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人认为这篇作品结构不完美,崔道怡却觉得结构别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
六十年代初期,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来稿信引起了崔道怡的兴趣,作者叫玛拉沁夫,崔道怡觉得小说的生活气息浓郁,但艺术上还欠火候,就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能修改。玛拉沁夫说:“崔编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我在呼和浩特熟人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干脆咱俩躲到包头,您指导我改好吗?”
那时候的编辑就是这么敬业,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铁鞋。崔道怡和玛拉沁夫住进了包头宾馆一个套间,玛拉沁夫住在里屋,崔道怡住在外屋。有崔道怡在身边,玛拉沁夫觉得有了主心骨。他写一段,崔道怡看一段,提一段意见,两人边讨论边研究如何改写,桌子上散落着雪片般的稿纸,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崔道怡的帮助下,玛拉沁夫很快就修改好小说《腾格里日出》,刊登在一九****年第十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文革”期间,文坛百花凋零,《人民文学》停刊了,编辑们各奔东西。一九七五年,李季主编把原来《人民文学》的编辑都调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崔道怡从《天津文学》杂志发现有个叫蒋子龙的人写东西不错,就约他到出版社见面。蒋子龙高高兴兴来到出版社,崔道怡得知他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就建议他写点最熟悉的工厂生活。那年头名牌编辑接见业余作者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受到鼓舞的蒋子龙一鼓作气写出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一个工厂的中层干部大胆抓生产的事。崔道怡鼎力相助,这篇小说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刊登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帽子棒子满天飞,在黑白混淆的日子里,这篇小说遭到批判,说是应合了右倾翻案风。作为小说组副组长和责任编辑的崔道怡挺身而出,替蒋子龙抵挡风雨。粉碎“四人帮”后,蒋子龙欢欣鼓舞,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批重量级的小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崔道怡广泛浏览各地的文学报刊,一个叫刘心武的新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刘心武的文章中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东西,便写信向他约稿。刘心武当时是北京十三中学的老师,接到《人民文学》编辑的来信很受鼓舞,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班主任》寄给崔道怡。崔道怡看后非常激动,立刻给刘心武回信说:“稿子写得很好,我已提交给主编审阅。”
刘心武接到崔道怡的信心潮起伏,因为稿子才寄走一个礼拜就收到了编辑肯定的来信!但没想到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太危险,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正式否定“文革”,这篇小说会不会捅娄子?崔道怡据理力争,在主编与几位同行的支持下,《班主任》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立刻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那时候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行量达一百八十万份,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威望。那时候的中国人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喜欢从文学作品中看政治动向。《人民文学》独领风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振聋发聩,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从《班主任》之后,《人民文学》杂志发起建立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极大地促进、繁荣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崔道怡有着四十二年的编辑经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极高,很少看走眼。所以很多著名作家都把崔道怡对自己作品的鉴赏,视为一种重要评价。王蒙曾经在一篇《关于<夜的眼>》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没有几个大家注意它,最好的也不过说你再试着创新吧。只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对之赞不绝口。他坚持把它收到建国三十年小说选里去了。当时与中国关系并未正常化的苏联很快把它译成俄语,选到他们的《外国文学》杂志里。八十年代美中第一次作家对谈时,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收了这篇小说,对它作了好的评价……”
崔道怡一生甘为绿叶,不愿抛头露面,可他却得到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正如李国文所说:“一些赫赫有名的作者,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和崔道怡的发现分不开的。”
不随俗眼看文章
十八年前,张守仁老师曾经到军艺文学系给我们讲过课。作为副主编,他主持的《十月》杂志是培养我走向文学之路的温床。那时候,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斗胆向《十月》投稿。有一次,我把自己写的一篇几万字的散文送给他看,当天晚上他就打来电话说:“孙晶岩,你的散文写得很好,但你没有掌握‘的’与‘得’的不同用法,不少作家都存在这个毛病。”
过了几天,作协组织去京郊采访,我刚一上车,他就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的”与“得”的语法规则。《十月》杂志却以显著位置刊登了我记述程思远先生的中篇报告文学《政海秘使》。这篇作品不仅在国内连篇累牍连载,还在海外引起反响。后来,程思远先生告诉我:宋健和方毅同志看到我的拙作后,亲自打电话告诉他作品写得很好。很多海外的朋友看到后,纷纷给他打来越洋电话祝贺。为此,程思远先生给我写来亲笔信:“蒙寄来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大作,既佩构思之佳,又感文笔之丽,使人得见全貌,感何可言。”
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像一阵冲击波,震惊了文坛,作者李存葆也成了全国妇孺皆知的人物。可是有谁知道这部作品的诞生内幕呢?一九八二年三月,总政在京西宾馆开军事文学创作研讨会。会议期间组织与会者到高碑店访问。路上,李存葆坐在张守仁旁边。张守仁问李存葆最近在写什么?李存葆说:“我现在手头有三个东西,一篇叫《月照军营》的小说,是写爱情的;二是写一个英雄的一生,名字我还没有想好;三是想写一篇关于自卫反击战的小说。”
张守仁说:“我就要自卫反击战这篇。我非常喜欢看世界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看得激动人心。可咱们中国的军事文学作品不敢触及军队的阴暗面,原子核的爆炸是由于原子核内部的矛盾引起的,不是与其他东西的矛盾所引发。你要大胆地写矛盾。”
张守仁当时是《十月》编辑部副主任,主管小说。《十月》杂志又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作为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编导的李存葆当然知道它的分量。开完会,李存葆来到解放军文艺社书库,关起门来写了一个月,完成了《高山下的花环》、《晚霞落进青纱帐》两部小说和一部叫作《金银梦》的报告文学。当他把稿子拿给解放军文艺社的人看时,一位老编辑觉得《高山下的花环》写得太尖锐,梁三喜牺牲了家人还要卖猪来还账,这不是毁我长城吗?
解放军文艺社的老编辑不敢发《花环》,把另外两部作品挑走发表了。李存葆摸黑来到张守仁家,把稿子交给张守仁。张守仁连夜看稿,不由得拍案叫绝,最后忍不住把已经睡下的老伴都叫起来听他朗读。看到写雷军长那一段,他觉得不过瘾,又给雷军长加了一段话:“走了!从沂蒙山来的祖孙三代人就这样走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上帝!”
第二天早上,张守仁欣喜若狂地把稿子带到编辑部,让同行传阅。大伙儿看后一致叫好,嚷嚷着要发下一期头条。过了一会儿,李存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张守仁打电话,询问对稿子的看法。张守仁说:“存葆,稿子写得非常好,我们要发头条。但你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有可能在全国引起轰动,你将被记者包围;二是有可能出事,你不要害怕,如果有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十月》编辑部的编辑有胆有识,他们齐心协力隆重推出这部佳作。一位搞评论的编辑自告奋勇把稿子拿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牧看,恳请他为《花环》写评论。冯牧看后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可我担心写得太尖锐,需要稍事修改,把太尖锐的地方抹掉才能发表。”
李存葆听了冯牧的修改意见觉得为难,便和张守仁商量。张守仁对李存葆说:你先按照冯牧的意见做些修改,争取他同意写评论。
冯牧看了李存葆的修改稿后给《花环》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但张守仁发的是李存葆未修改的原稿。小说刊登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十月》杂志头条,同期又配发了冯牧写的评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都在争取《花环》的电影改编权,李存葆被电影导演和记者团团包围,著名导演谢晋给李存葆发来一封一千多字的电报,要求购买电影改编权。紧接着,《花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京剧、话剧、舞剧、歌剧、曲剧、连环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张守仁看到李存葆正处在创作巅峰状态,就和他在南京策划下一个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他俩在中山陵的松树林里你一言我一语构思完成后,李存葆躲到山东烟台写稿。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袁厚春坐不住了,存葆是军队作家,肥水不能流到外人田啊。他四处打听李存葆的下落,得知他在烟台,就盯着李存葆说:“存葆,首长命令你下一部作品不能给地方。”
李存葆接到袁厚春的电话觉得特别为难,思前想后,他给张守仁打了长途电话,原以为张守仁会责骂自己忘恩负义,谁知张守仁却和蔼地说:“存葆,你把稿子给《昆仑》吧,你是部队作家,我能理解。”李存葆很快就完成了十四万字的《坟茔》,袁厚春把这篇作品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第六期《昆仑》杂志的头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长篇联播,在全国再次引起轰动。
张守仁与铁凝的友谊也是一段文坛佳话。一九七八年,张守仁和章仲锷一道南下组稿,第一站就是保定。那天,二十一岁的铁凝穿着一件绿色的军衣,蓝色的军裙,绿色的军袜,留着短发,显得青春亮丽。张守仁鼓励她说:“你好好写,往后有好的稿子寄给我们吧。”后来,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由张守仁在《十月》杂志隆重推出。这篇作品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红衣少女》,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
一九八五年四月,铁凝和张守仁在南京参加发奖会,她向张守仁谈了小说《玫瑰门》的构思。张守仁觉得铁凝的艺术感觉不错,便对她说:“你给我讲的是地面上的事,就像一棵大树,树的底下要有根系,要向深处开掘。”
铁凝拿着本子认真地记下张守仁说的话,张守仁觉得她很虚心,虚心的作家往往能成大器。铁凝到北京出差,住在空军大院的亲戚家,总是忘不了张守仁老师。一天,她给张守仁打电话说:“我给您带了一些家乡的赵州梨,您有空来取吧。”
张守仁来到铁凝的亲戚家,一见面就聊起了文学。当他提到初次见面铁凝的那身装束时,铁凝笑着说:“那套衣服是姑姑从北京给我冒领的二号军装。”张守仁带着那兜赵州梨上了地铁,全神贯注地看着刚买的报纸。到站后,他拿着报纸匆匆走出车厢,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把铁凝大老远从保定给他带来的赵州梨落在车厢里了,觉得很遗憾。
铁凝写道:“一九八三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在《十月》发表,写时我是一名业余作者,在一家地区级的杂志社当小说编辑。但《十月》的编辑老师没有漠视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他们将《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以头条位置发表。吉祥《十月》为我的写作带来了好运。《十月》的朴实宽厚与《十月》的鲜活敏感是并存的,正是这样的气质吸引着、鼓励着、推出着一大批文学青年或不再年轻的作家和作者,为此我充满感激。”
河南省作协主席张一弓八十年代初期下放到河南嵩山,他克制不住文学的诱惑,请假钻出山窝,写出了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这篇小说本来是某杂志的约稿,可主编看了稿子后觉得有的地方写得过于大胆,怕惹事。张一弓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呕心沥血写的小说会变成“烫手的马铃薯”,便做好了带上“马铃薯”返回嵩山的准备。这时,有一位温文儒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士找到他,轻吐着没有被普通话改造彻底的“吴侬软语”,说他从那家刊物一位编辑朋友的口中得知了“张铁匠”的事情,而且看过了此稿。准备把它带回《十月》发表,希望能得到张一弓的同意。此人便是张守仁。张一弓一寻思:作品是作家的女儿,女儿长大了父母就想给她找个好婆家。现在定的娃娃亲的婆家不想娶自己的女儿,女儿正愁嫁不出去呢,《十月》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是条件最好的婆家,能在《十月》发表,这可真是把女儿嫁到福窝里去了。他幽默地说:“守仁不怕烫手,我感谢还来不及呢,岂有不同意之理?”
稿子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十月》杂志的头条,张一弓还没有看到《十月》上的张铁匠长得什么模样,就接到长影厂的电话,说想把小说拍成电影。这篇小说后来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还获了奖。
张守仁像一只蜜蜂,辛勤地在花丛中采蜜。他编辑了王蒙的小说《蝴蝶》,宗璞的小说《三生石》,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蒋子龙的小说《开拓者》,权延赤的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等一大批在全国有强烈反响的作品。
一九五七年,张守仁在武汉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早在二十岁那年,他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深深为小说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所打动,立志将来要当一名编辑,做著名作家的第一个读者。四十五年的编辑生涯,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很多好稿子。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没有退过一篇好稿子。在张守仁家的书房里,挂着作家汪曾祺赠送给他的一首诗:“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齿凉。”诗中的“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两句,是他的真实写照。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